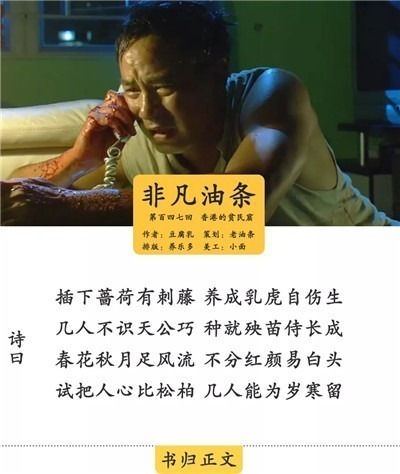
跨过边界:香港幻想的破灭
2004年,香港天水围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名香港男子持刀杀死其来自内地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后自杀身亡。
案情并不复杂,但案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却并不简单。
那个年代去内地寻欢作乐,是很多香港男人常见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其实他们也并不富裕,甚至属于香港底层,只不过当时内地更为贫穷,他们大可以降维打击,好好奢侈一番。包养二奶,是当时香港货车司机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混迹于深圳东莞的内地女人们,也都因此改善了生活,有的甚至拿到香港的居住权,成为了在乡里令人羡慕的香港少奶奶。
但现实总是很残忍,最终她们会发现,她们嫁的男人因为离婚而且年龄不小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钱,经济环境差的时候甚至还会失业。结婚后他们在香港的居住环境也不佳,生活更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在内地是穷人,在香港还是蜗居,与她们的预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一例灭门惨案中的夫妻就符合上面的条件,丈夫与妻子年龄差距大,丈夫失业在家,家用拮据。他们生活的天水围则是香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社区,失业率高,治安条件差。
天水围位于最近突然成名的元朗区西北部,北边紧邻香港湿地公园,西北边就是深圳湾,隔着海湾能够看到深圳。这个名字里带着“围”字的地区,像极了香港这座围城的隐喻。
 (图片©图虫·创意)
(图片©图虫·创意)
政府在天水围兴建了大量公屋,吸纳了将近30万人在这里居住。公屋租金较为廉价,租住公屋的多为香港的低收入人群,但是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并不完善,治安实在是个大问题。这起灭门惨案并非孤例,这里的暴力犯罪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6年,林郑月娥还是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也对天水围的问题感到费解,将天水围称作“苦难之城”。不知道上周她去天水围探访被围攻的警署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当年她说过的话。
如今作为特首的林郑月娥,对天水围的思考也要升级了,她一定想过:这苦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政企合谋:形成专营的密约
1979年,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一家实力雄厚的内地企业与大宝地产、长江实业等香港本地开发商一道,成立巍城发展公司,买下了天水围的土地。
那时候的香港房地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买入地皮进行开发似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巍城发展公司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家公司甚至在1980年提出一个为期15年,分三期完成,人口53.5万的新市镇蓝图。在规划里,原本是一大片村庄和鱼塘的天水围,在规划中将建起公共及私人住宅、工业和商业发展、运输系统、小区和园林设施等。一个环境优良、基础设施良好的新市镇眼看要在深圳湾对岸冉冉升起。
然而,当时香港政治前景尚不明朗,很多产业都处在停滞观望的状态,港英政府最终暂停了天水围计划,这一拖就拖到了1982年。
糟糕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1981年开始,香港房地产业进入下行周期,直到1984年才回暖。
 数据来源: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
数据来源: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
港英政府此时陷入了两难困局:房地产业不景气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捉襟见肘;然而香港面临回归,当务之急是稳定住投资者的信心,此时如果否定掉巍城发展公司的计划,或是减少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影响到香港的投资环境,更何况巍城的大股东还是内地大企业,如果开发计划得不到优厚回报,会打击内地对香港商业前途的信心。
港英政府的选择是,停止原先的开发计划,但向巍城收购天水围全部的488公顷土地,作价22.6亿,高出合理的价格不少——这可是远离市中心的未开发土地。当时这些企业资金压力很大,远不如现在财大气粗,亏了这块地多少年都未必缓得回来,这样的收购对内地也算是善意的橄榄枝。
天水围这块地现在又到了政府手里,但政府也是一筹莫展,想来想去还是得引入私人资本开发,只得把38.5公顷土地让与巍城用于私人住宅开发。
李嘉诚说过入股巍城的那家央企“缺乏地产发展经验”,言下之意是他的长江实业该好好露一手了。
长江实业先是以1.6亿元收购了大宝地产的25%股权,这样他和长江实业在巍城的控股高达49%,仅次于某央企的51%。长江实业继而与该央企达成协议,担保其在这个发展计划中的最低收益不少于7.5亿元,换取了长江实业控制了天水围私人住宅开发的权利,建成了后来的嘉湖山庄。
而嘉湖山庄外的住宅,大多数被开发成了公屋。瞧瞧这令人生畏的建筑密度。
 (图片来自wikipedia@Wikipedia user -Wpcpey)
(图片来自wikipedia@Wikipedia user -Wpcpey)
巍城有限公司还与港英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要求政府限制在公屋社区内发展商业设施规模,以免妨碍嘉湖山庄内的商业设施收益。
这份密约直到2010年才被香港的英语媒体《南华早报》爆出,在Facebook上一度引发轰动,民众愤怒于政府和商业巨头私相授受,保证后者的垄断。
从自己开发的私人住宅社区里尽量多地捞取铜板,长袖善舞保证专营地位,有钱人的赚钱办法就是这么枯燥且有效。
天水围城:城市规划的失败
天水围最终成了一个很别扭的区域,为日后发生的悲惨事件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香港本来在天水围规划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并扣除地价售予市民的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买得上房),然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房价大跌,政府为了稳房价,又取消了很多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并将其改成公屋。公屋可不是中产阶级想住的房子,天水围一下失去了调节社区文化的中坚力量,变成了单纯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
当然这不妨碍天水围核心的私人住宅小区嘉湖山庄。它是李首富的得意之作,位于天水围中心,却是个封闭小区。除住客外,其他人一律不得进入小区。墙外的低收入人群,在天水围就只能绕道走路。
 嘉湖山庄景湖居
嘉湖山庄景湖居
(图片来自wikipedia@WiNG)
墙里墙外,阶级分化对比鲜明,看似生活在一个空间,实际上却是以收入为界天渊相隔,就更别提先富带动后富了。
低收入居民没法从富裕居民那里赚得到钱,小区里也没什么产业规划,就只有两条路,自己做小买卖或者去市中心打工。
但这两条路都很艰难。
去市中心打工一天下来通勤就得三四个小时,来回也需要三四十元,每天身心疲惫不说,赚的钱不少还得贡献给交通费。
做小生意也很难,由于密约的存在,造成天水围沿街商铺几乎不存在,小商小贩想要个铺位,只能去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的领汇商场里租用昂贵的铺位——由于成本的高昂,这些铺位更有可能被连锁店租用。
最有钱的嘉湖山庄里,商铺则干脆都由长江实业自己代劳了。
重床叠架的物业拔毛让天水围的商场物价比元朗中心的还要高10%以上,以至于居民进行大规模采购都更愿意去那里。
想在街上摆摊?那就只能天光墟了(就是北方的鬼市儿),天一亮就赶紧跑吧,食环署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沿街摆摊的另一大困境,是街道对行人的不友好。这里宽阔整洁的马路是为行车设计的,行人只能绕远道找十字路口或天桥,大大增加了步行的困难——然而这里绝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是没有车的,宽阔的马路利用率并不高,倒是让富人开上了康庄大道。
 你可以用你的一生
你可以用你的一生
买其中的几个格子
(图片©图虫·创意)
来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会陷入“找工作困难→工资不稳定→只能支付较低房租→搬入天水围的公屋→远离市区找工作更困难→难以有足够的积蓄搬离天水围”的恶性链条,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失业,靠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类似于最低保障金)维持生活。
发生灭门惨案的2004年,元朗领取综援个案近3万宗,天水围占了一半;天水围的自杀率也是全港最高
中年危机:焦虑背后的优越
香港导演许鞍华在探访天水围后,拍摄了一部以2004年灭门惨案为原型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案情。不过片中的人物形象则是综合了当时很多具有相同处境的人物而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形象。
男主角李森,原本是一个香港装修工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能靠出卖劳力和手艺赚得较为丰厚的收入。按照李森的说法,他当时给原配买首饰出手还是相当阔绰的。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然而原配管束李森较严格,使他对婚姻产生了不满情绪。他开始流连于风月场所,在年轻貌美的肉体上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
他在深圳寻花问柳,却在1998年让他包养的四川女孩晓玲怀了孕。晓玲趁机要他做出选择:是抛弃她回到原配身边,还是和原配离婚迎娶她?进退两难的李森只能点一根烟感慨生活太难了。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其实在居住在深圳被香港人包养的女孩眼中,晓玲可能是她们中的幸运儿,因为李森决定和原配闹离婚,抛弃原来的家庭迎娶晓玲。毕竟深圳河南边的香港是对他管束严格的黄脸婆原配和叛逆期的儿子,深圳河北边的温柔乡则有着对他百依百顺崇拜不已的年轻女孩,他做出这种选择也并不意外。
为此,他还表现得相当有诚意,跟着晓玲回到她四川老家探望晓玲的父母。
那时候的四川乡村还很贫困,很多像晓玲这样的青年男女没有工作机会,又不想在家里种地,就会去珠三角一带打工,寻找机会。就在晓玲背井离乡的那一年,讲述在广东打工的女性群体的电视剧《外来妹》播出,可能70后80初的朋友们还会想起这部电视剧由杨钰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
李森还带上了一大笔钱,在晓玲面前夸口说要去她家建设新农村。
来到晓玲的家乡,李森受到了全家的欢迎,晓玲父母也因为女儿找了个香港对象而在全村倍儿有面子。晚上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那年洪水的新闻,说香港人民慷慨解囊给内地受灾地区捐款,晓玲父亲半是羡慕半是讨好地对李森说,香港人真有善心。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李森一高兴,钱包就完蛋了。他答应为晓玲家出钱出力装修新房,置办家电,这可能是晓玲父母穷尽这辈子的积蓄都完不成的任务。于是在这个家庭,老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仿佛他就是晓玲家庭的救世主,他的中年危机感也没那么强烈了。
然而日久见人心,随着李森带来的钱慢慢花光,晓玲父母也对李森冷淡起来。李森则对晓玲家有着莫名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到来和付出是对晓玲家人的恩赐,甚至兽性大发强奸了晓玲的妹妹。
为了晓玲未来的幸福,晓玲父母对此忍气吞声。
后来,内心越发不平衡的李森把一只狗装进麻袋,抄起木棍用尽力气打死了它。狗的哀鸣和鲜血渗出了麻袋,似乎在隐喻晓玲的婚姻注定是个悲剧。
凶相毕露:经济去势的暴躁
晓玲发现,她婚后生活可不是村里人想像中那样,嫁了香港人就可以做少奶奶享福了。这就像高考大省的某考生辛辛苦苦考到了某著名的985大学的劝退专业,然后他家里的人都为他高兴,却不知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可能有乔碧萝的P图头像和真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
可能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无敌的李森还是失业了。但他与原配离婚依然坚决,估计财产大出血,以至于不得不搬到天水围的公屋居住。婚后晓玲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由于手续原因晓玲无法在港定居,则先是由他在港抚养两个女儿,无业的他只能靠领取综援过日子。
直到2004年初,晓玲才拿到单程证来到天水围与李森和两个女儿同住。
李森每月领取8000元的综援,只给妻子2000元以维持家用,晓玲见家用拮据,就去餐厅打工,忍受着食客的下流笑话。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李森则无业在家,以天水围的商业环境就连做小买卖都不可得,闲极无聊就去湿地钓鱼。
他对晓玲出去打工颇为不满:要是被发现了,取消了自己的综援,吃不上福利了那可得了!再说了,妻子这么年轻貌美,人到中年,比妻子大十多岁的李森相当多疑,自己男性的独占欲仿佛受到了挑战,每次听说妻子和什么男人打交道,就会暴跳如雷。
豆瓣网友的评论说得好,李森象征着香港的“经济去势”,原来的自信逐渐消退了。
失去自信的李森越发多疑暴躁,仍然想要维持他可怜的优越感,动辄辱骂、殴打晓玲,对晓玲婚内强奸,还用刀逼晓玲说:
“没有你,我没有今天!”
大概受教育水平低的人都很容易在身边找到生活失意的原因,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报复。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老李的行为越来越粗暴,以至于晓玲还发现李森有猥亵女儿的行为,这个女人不得不开始寻求外部帮助。
晓玲打电话给父母,父母却劝她忍气吞声;好心人带她区间天水围的议员,议员倒是认真负责,送她去了庇护中心,并联系社工帮助她。然而天水围的社工并不尽职尽责,反倒认为只是普通家庭纠纷,抱着“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心态和稀泥。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由于害怕自己离婚后,没有在香港待满七年,没有获得永居身份的晓玲被遣返回内地,晓玲的态度一开始也并不坚决,也倾向于保持家庭完整,只能把暴力的苦果自己消化,接受了社工的调解。后来被殴打后她脚受伤流血,她报警后反悔了,称是自己不小心踏到玻璃弄伤脚,不会追究,案件列为家庭纠纷。
晓玲的忍耐换来的是李森的变本加厉。被施暴后她再次被送到庇护中心,疯狂的李森一个劲打她电话,威胁她要对他们的孩子动手,满口说的已经不是人话了。
此时正值公共假期复活节,社工放假,晓玲不得不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回到天水围。她前往天水围警署报警,对,就是那个上周刚被林郑月娥视察过的天水围警署。
晓玲的报警没有被严肃对待。之前晓玲报警后改口让警察降低了警惕,似乎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再次认为这只不过是家庭纠纷。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失去了所有社会支持的晓玲回到家,等待她的是面目狰狞的丈夫。李森挥刀杀了晓玲之后,陷入了彻底的疯狂,随后又杀死了他们的双胞胎女儿。
当母女三人躺在血泊中后,李森才开始怂了。怂人毕竟是怂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想出了一个拙劣的办法,捅了自己肚子一刀后,打电话报案谎称自己被晓玲捅伤,并撒谎说晓玲杀死了他们的孩子。
却没料到力道掌握的不好,这一刀他捅得很深,以至于受了重伤,被赶到的警察送医后仍然在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在此要插一句,直到2017年,天水围才有了第一个正式医院,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这里的将近三十万人只有一个诊所。富人可以开着车去别处求医,穷人生了病境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窘状,也阴差阳错地要了杀人恶魔的性命。
事后反思:逐渐下沉的城市
灭门惨案发生后,香港舆论大哗,人们开始反思天水围的治安问题。案件中的多种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
天水围的社工任务繁重,力量也不足,工作难免不上心,这就导致很多调节失效,酿成大祸。
天水围的警察对犯罪预防预见性差,对死者生前的报警掉以轻心,没有给死者有效的帮助。
领取综援的群体也成了社会关注的对象。而2007年,又一个天水围的领取综援的家庭酿成血案:一个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医院留医,患精神病的妻子将一对子女从24楼扔下后跳楼自杀,3人当场死亡。
许鞍华则在策划《天水围的夜与雾》时,接触了类似的香港家庭,发现那些底层的香港男人在自己来自内地的年轻妻子面前仍然要极力维持优越感,她不由得感叹:
“我突然觉得好好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他自己那么窝囊,还要挑选别人。”
这些人心里是不把他们的内地配偶当人看的,似乎对方只是他的附属物而已。
而惨案的发生地天水围,则是香港地产霸权操纵香港财富分配甚至城市空间的最极端例子。除了严密与外界分隔的私人住宅小区外,这里无疑沦为了事实上的贫民区。
穷人以为富人是靠和他们一样的办法努力赚钱,却没想到富人做的是降维打击。
而在城市规划上,地产霸权也以隐秘的手段请君入瓮。有人看到天水围宽阔的街道和繁多的过街天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行人要穿过宽阔的马路,往往须倚靠行人天桥或隧道,而刻意架空街道,目的是将在路面行走的行人引上行人天桥,再把他们送入商场购物。”
 (图片来自wikipedia@Baycrest)
(图片来自wikipedia@Baycrest)
据央视报道,上周林郑月娥探访天水围,除了视察了受袭击的警署之外,还“了解天水围新公众街市的选址。该处邻近港铁站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便利,方便区内市民购买新鲜粮食;根据初步规划,新街市将提供最少120个摊档,包括熟食摊档” 。
尽管这120个新摊位对于帮助天水围的就业是杯水车薪,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好的改变。
其实2008年美食教父蔡澜就曾提议在天水围建设300个熟食摊档,预计容纳三千人就业,结果被无情地否决了。
规划不利的背后,除了受到地产霸权裹挟之外,还有一大原因是天水围距离香港市中心太远,而港府财力有限,鞭长莫及。假如没有行政上的界限,临近深圳的天水围乃至整个元朗区本可以在深圳的带动下更加兴旺发达。
但最终,天水围还是成了牺牲品,沦为了贫民区。
说句题外话,扮演李森的是香港著名影星任达华,幸亏《天水围的夜与雾》在内地不够知名,不然他就取代安嘉和,哦不,冯远征老师,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了。他最近参与安保不到位的商业活动被刺,万幸很快康复,但也不免让人感叹港星的时代也要落幕了。
参考文献:
邓永成. 香港天水围新市镇社会问题的历史地理观[J]. 中国名城, 2009(7).
林郑月娥考察天水围区 探望驻守当区警员, 央视网, http://m.news.cctv.com/2019/08/07/ARTIA1nRvEgFZLW3OIMhnTYi190807.shtml
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南华早报, https://www.scmp.com/article/732536/colonial-deal-built-city-sadness
Liu K . 「悲情城市」是怎樣「打造」的? 天水圍的空間政治[J]. 2011.
香港需要天水围——一部电视电影的胜利,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27331
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南华早报, https://www.scmp.com/article/732557/job-creation-plans-tin-shui-wai-rejected
封面图片来自《天水围的夜与雾》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豆腐乳儿。来源:公众号 地球知识局。责任编辑:还朝)
(作者:豆腐乳儿。来源:公众号 地球知识局。责任编辑:还朝)






所谓中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所谓的先富带动后富,是先富(社会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可以使自身富起来)带动后富(资产阶级剥削前者暴富),是这样的。 undefined
众所周知,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对立性质、并指出这种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发现。本文当然也无意对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就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共识的理论做任何创新;以下所有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和不同阶段状况的概述,都不过是对经验过程的一般归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讨论无关。
既然不是以理论探讨为目的写的文章,本文所列出的基本数据也就不必精确: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1992年,陡然出现了4600万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占那时11亿人口的不到4%。从那以后过了12年,如今13亿人口中有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
,其中约5亿在农村。5亿之中已有至少2亿成为非农就业劳动力,其中有1.2亿离开家乡外出流动打工,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流动农民”,占总人口之比约为15%。
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引起广泛关注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专家给出因利益背景不同而无所谓对错的不同解释,也是必然的。
一、中国农民进城打工高潮在九十年代形成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放开计划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制度。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大批流动是从1992年以后真正开始的。以前不是没有流动,但数量较少。因为,中国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按计划凭票证供应的制度是在1992年取消的。到年底,只有西北的少数县份还没有取消粮票。
当人们不再使用粮票时,农民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就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是1992年中国突然出现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要条件。
其次,这一现象的出现又和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的农产品卖难有关。
中国在1988年实行了以“价格闯关”为名的市场化改革,随之出现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改制中都出现过的物价大幅度上涨;导致1989年以后连续3年的经济萧条 。此期间城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弹性下降造成的大多数农产品卖难 ,直接导致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但其必须以现金开支的教育、医疗、税费等却不仅不可能同步减、反而不断增加,因此农民就不得不寻找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以增加现金收入。
其三是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
1992年以前农村并不是没有大量出现非农就业,但与九十年代以后的最大不同是,八十年代主要是在农村内部从事非农就业,亦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本村或就近的乡镇企业就业。因为,随着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1985年农民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七千多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同步地增加了经济作物。农民可以在经济作物的购销经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寻找到就业机会,农业结构调整之后的农村经济活跃造成了现金收入和支出增加,这就造成“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导致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大量兴起,以填补一般低档消费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市场空间。
这也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不是主要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没有放开粮食、油料等消费物资的计划分配体制的约束条件下,第一波的非农就业是在农村内部完成的:1984-1988年曾经出现平均每年超过17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1988-89年中国城市爆发通货膨胀危机随后导致1990-91年的生产停滞;即使在1988-1991年的危机和萧条阶段,农村仍然平均每年有120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到1992年出现农民大规模流动之前,农村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约1亿3千万农业劳动力。
相对来讲,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低成本的转移,既没有诸如各种政府部门收费或者行业准入造成的过高门槛,也没有企业上交社会保障费用等问题。这种最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客观上有利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的低成本起步。这些就是被很多后来留学归国学者所忽视的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优点。当年的中国还没有那么激进地照搬西方制度,政府允许乡镇企业在本村无偿占地、允许税前列支“支农资金”和补足村社公共开支等,那时的政策大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好政策。
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但因为在原材料、产品市场等各方面与城市形成很大的竞争,引起了国家计划内工业部门的不满,政府随后在政策方面的调整,客观上越来越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利,出现全国大抢购,乃至于发生银行挤兑风潮之后,国家立即采取了紧缩政策,“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得不到贷款,失去银行资金支持以后,1990年后一度出现了不景气的局面 。
可以认为,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政策导向变化之后,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和从乡镇企业得到的现金收入下降,是1992年前后出现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的第三个原因。
二、城市改革的复杂背景和进城农民工的两个阶段
一是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的认识。
1988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达到18.6%,个别大城市比如北京物价指数超过25%,事实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型的危机发生导致1989年的紧缩局面,1990年实际上是进入萧条的第二年,此后,还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从萧条到复苏的过程。这个期间逐渐蓄积起来的经济增长的力量,在1992年“邓南巡谈话”的条件下得到释放 。
不过,这并不是靠原来一般的制造产业自身的运转释放出来的,而是借邓南巡谈话之机突然产生的三个投机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第一个就是大办开发区,大搞房地产。1992年前后同时开放的还有证券市场;接下来1993年前后开放了期货市场。其实邓南巡之后,恢复对传统产业的投资并不能马上使得经济重新进入高涨。而恰恰是这三个明显具有投机性的领域的“突破”,使得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形成的投资压力得到突破性释放。
随着邓南巡,“开发区热”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全国形成了8千多个开发区,带动了一系列的地产投机。任何带有强烈的投机性的经济领域的开放,必然带动大量金融资本注入,以追求短期资本收益 。当时,这是带动农民外出打工潮的一个外部原因。
同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接着带来能源、原材料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热潮,带动了产业扩张,要增加大量的机器设备进口,随之,1993年前后出现进口热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随后导致1994年不得不实行“官方汇率与市场并轨”的改革,本币一次性地贬值57%。
二是进城农民工两个阶段的结构变化与问题。
尽管邓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过热并不健康。但其同时带动的农民外出打工潮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办开发区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产业工人,而是粗工,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是男性。
东部沿海开发区要搞“三通一平”,这是初期阶段。以后是连续三年的经济高涨,进城打工的人从1992年的4600多万,增加到1994年的6000万左右。这样的过程与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工业化平均每年1000多万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为非农就业相比,人数少得多但成本却大大增加。当时中国政府认识到那是“经济过热”。
第二个阶段是在开发区大致建成后,到九七年香港回归。
由于中国绝不放弃香港回归时全部主权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香港一般制造产业向广东转移。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策动香港大资本出逃,想使香港经济空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则是“国家资本政治挂帅”,短期内组织了460亿资本进入香港,填补了香港大资本出逃产生的空缺,同时也抬高了香港房地产价格。因此迫使大量香港中小产业资本移师大陆。所以,统计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的资本,大量是港资或者海外华人资金。这就恰好填补了上述搞好三通一平的东南沿海开发区的资本空白。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但这毕竟是真正的产业资本转移。因为南方开发区引进来的大量是玩具、服装、电器等等的生产线,所需要的工人以女性为主,这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打工者的性别结构,女工的问题就开始突出了,造成了打工群体的新问题。
因为农村的家庭一般必须是男工回去顶家的,大部分男工是挣了钱就走的,消费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事实上,女工比较容易落地生根;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可能很好保障女性的权益,妇女在农村中的财产地位和在城市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没有财产约束的情况下,女工更容易进入城市成为打工群体,这与城市打工群体常年化、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和随带人口增加造成的子女教育、居住条件、医疗等问题,都直接相关。
因为1992-93年城市需要劳动力的主要是粗工,所以,以往男性为主的打工者可以三十岁、四十岁,只要能干体力活就可以。那时不仅农村青年出来,壮年也出来,他们一般都有家有口,肯定会回农村去。因此,第一拨的打工潮基本是来多少回多少。但在东南沿海形成一般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布局以后,第二拨就可以来而不往。此后,进入城市的打工群体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不大,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增大。女性和青年人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这使打工群体在消费上、在融入城市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趋势性变化。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三、新时期的劳资关系问题
首先看强势集团的形成。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房地产投机的还主要是“官员下海”或者以官方资本为主,因为,往往是官员和官方资本容易得到政府垄断占有的土地。那时的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政府征占和官方控制的金融投资结合形成资本的过程。因此中国才出现权钱结合、在地产业发展中快速致富的权贵资本集团雏形。接着,是九十年代后期以国有企业改制来实现的官方资本个人化,逐渐游离出一批股份制公司,并导致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的大资本集团开始成形。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是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第二桶金就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房地产投机。原始积累捞出来以后,很快就形成资本集团。城市中的强势群体逐渐产生后,就必然会产生另一个对立的弱势群体。资本集团和其利益代表成为一个强势群体之后,它所要求的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基本制度框架开始发挥作用。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悄悄地被“国有企业”取代,其低效益的问题几乎毫无疑问地就变成了工人的问题。于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保护投资人权益,以提高资本收益等等,成为政府主动推进的城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当资本集团形成并日益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影响开始增大,这时候,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也随即发生了被利益所决定的变化。制度文化的总的趋向也就越来越不利于城市的劳动群体。
其次,分析城市工人群体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九十年代初以前,城市中的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工人群体,其实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几乎全部公有制劳动者都享有生老病死全程的福利保障,尽管收入也很低,但相对于农民来讲,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优越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所以,他们在传统体制内部发挥着类似于中产阶级的作用,甚至毛泽东发起的文化革命,都受制于无法动员他们中真正的精英。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资本强势集团形成以后,城市国有企业工人的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了。一系列的城市政策开始不利于那些曾经得益于旧体制的工人。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大抢购之后,与政府财政关系直接的国家金融系统面临群众挤兑;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率,但并没有同时调整贷款利率,这导致1988年当年金融系统的直接亏损就到达460亿左右;年末转化为当年财政赤字500亿。从此,中央财政出现了一个不利的发展趋势:财政赤字此后不断增加,就连续向银行透支;银行资本金下降,金融系统的形势开始恶化。又加上1989-91年连续三年的所谓“三角债”期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财政的赤字也不断增加。于是到1993年前后,财政不仅吃空了银行的资本金,还多透支了83亿,这等于政府吃了老百姓的存款。1994年后,财政不得不转变为靠发债维持。国债的发行数量是按倍数往上翻的,五十亿、一百亿、二百亿、五百亿、一千亿;翻到后来,最高年份发到三千多亿。
因为财政收支出现了长期严重赤字,靠发国债维持开支,所以,财政过去承担的基本保障开支,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的支付便都逐渐弱化。客观上造成了财政“甩包袱”式的各种改革。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和医疗都开始产业化、市场化,公开地大规模提高收费标准,公共品变成了部门谋取暴利的手段。这是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另一面。
官方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或公司化,和公共品部门的企业化、产业化或者私营化,迅速地暴露了或恶化了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失业下岗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了。这时候的主流话语就在讲进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和下岗职工这个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而独独不讲矛盾是如何造成的,背景是什么?更不提金融资本是怎么形成的?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是怎么形成的?强势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不仅这些都忽略了,还乐于帮助在这个领域翻云覆雨的所谓的大款们进行“财产合理化、合法化”包装;后来则进一步强调无条件“大赦”,不管昨天的原始积累中企业家手指缝里有多少血,都可以不再追究权钱交易的那些腐败问题了。以后就你财阀、我精英,从《与狼共舞》变成与钱共舞……。
总之,这是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打工群体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和城市的整个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制度环境变化有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