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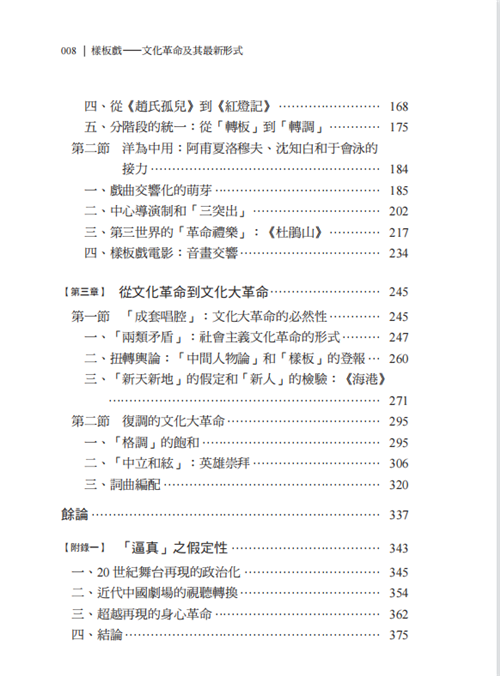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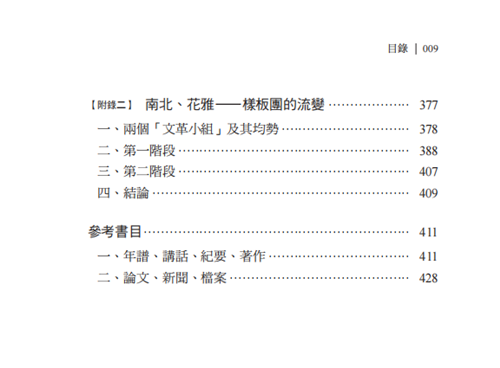
四、文化革命研究和样板戏研究之对观
黑格尔提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展现真理”69 。以此言之,“反映”和“示范”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样板戏,展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考察“后文革”时期西方学界对文化革命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研究和文艺研究的隔离,这是文化革命相关研究的一种主要倾向。
在文革政治的研究领域,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文革中出现的“派性”(factionalism)问题。在中共的语境中,派性就是派别性,与党性对立,指革命队伍内某些人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上,以一派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一派的得失为转移,结派营私。“派性”作为一个贬义词,与无产阶级的“党性”相对立。文革的“派性”与上述定义有所区别,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各级党组织被“夺权”后、自下而上开展文化革命的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内部矛盾。由于群众运动无法克服“派性”,“一斗二批三改”从“文斗”转向“武斗”,地方文革对“武斗”的复制令其走向了“扩大化”。
近年来,文革研究的主要分歧围绕着七十年代西方中国研究所确立的“社会冲突论”(social interpretation)展开。“社会冲突论”中,关于文革“派性”的社会学解释是:群众运动分为两派,其中保守派倾向于维持现状,例如保卫党委、支持部队;造反派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为激烈地改变既有的体制。70为了反驳“社会冲突论”这个理论假设,学界有过“两个文革”、“两种理论”、“两类精英”、“中心/边缘”等论述。
例如,杨小凯将文革区分出“官”、“民”的“两个文革”,一个是上层权力斗争,另一个是群众反官僚政治阶级的运动。71林伟然认为,前述“两个文革”是一种“方便的理论”,接受了官方对迫害老干部事件的渲染,旨在重弹文革的“低法治”等等老调。林伟然提出文革中并存着“两种阶级理论”,其中的“旧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前国家用于社会改造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新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以来社会用于重建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故而文革实践中“派性”斗争的爆发,是新旧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竞争的具体表现。总之这反映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并不成熟。72王绍光向“十七年”追溯“派性”的形成,提出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也是由类似新旧精英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由此,群众运动中“派性”并非文革的新生事物,而无非是上层文革中“新旧精英”冲突在底层的镜像。上述说法实际是官民对立的“权力斗争论”的一种变形。73
为进一步解释“底层文革”,杨小凯认为,在中央文革小组对左派整风之后,远离中心的“无政府主义造反派”感受到了“地方镇压机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双重压力,压迫的增强导致了叛逆情绪的增强和地方武斗的加剧。以“底层文革”为对象,吴一庆考察地方文革中出现的激烈“派性”,试图突破“社会冲突论”和“权力斗争论”的研究范式。他大量搜集整理湖南群众组织“省无联”的运动轨迹,将官民“两个文革”转化为“中心和边缘”的文革,指出位于中心的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局限,相反身处政治边缘的年轻人则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入而理智的解决方案。74而安舟着眼于文革中的主体,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一分为二,塑型为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继而将捍卫政治资本的红卫兵归为一派,捍卫文化资本的另划一派。他认为这种文化、政治的分野在文革后期水到渠成地造成了“红色工程师的崛起”。75诚然,文化、政治的分分合合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一分为二”不足以阐释“派性”的兴衰。不过,对文化革命的主体性之“流变”的分析,避免了文革研究滑向另一种错误的倾向。
例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过一种“去政治化”76的文革论,将“派性”解释为不同人在不确定的“政治背景”(political context)中采取的不同立场。那么,一旦派系形成,真正的群众政治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为证明其政治立场而战斗的“表演”罢了。77文革时期身在武汉的王绍光讲述了一段个人体验:上海的“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夺权”高潮时,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王绍光认为,显然那位工人并不知道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78
上述研究和口述,误将文革“派性”等同于某种群众性的“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s)。行为艺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艺术形式,是20世纪六十年代根据艺术家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作品来定义的。它包含以下四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从剧场的意识形态史看,行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观念艺术。换言之,“走出剧场”与“告别革命”具有突破时空的互文性。
退一步说,将“派性”过度“问题化”,从“派性—武斗”的小孔“再现”出一幅所谓的“文革全景”,这无疑是接受了“毛的最后的革命”79这一假设的结果。“Mao’s last revolution”这个提法,最初是麦克法夸尔在1966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革现状综述的短文的标题。该文文末提及,在“接班人”林彪接过领导权后,中国进入军管的局面,这种状况可能意味着毛泽东亲手破坏了他发动文革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初衷。80七十年代中期,迈斯纳使用“毛的最后的革命”这一说法,从整全的20世纪中国内部考察文革。81后冷战时期,“毛的最后的革命”成为“继续革命”难以为继的符号,其思想资源是法兰西斯·福山(F.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源于他在1988年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历史终结论”做出了全球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宣判。在麦克法夸尔于2006年正式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毛的最后的革命”这一说法变成了依附于“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后见之明。
无论是将文革假设为“毛的最后的革命”,还是“一场夭折的、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82,这些假设都无法绕过下列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即列宁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标志)是否真实存在过?对这个问题,我在导论的前一部分已经给出答案。
由此,样板戏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破除主流文革图景的那些“成像小孔”。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遗迹,样板戏为既有的文革研究增添了音乐形式这个“听筒”。
作为“毛的最后的革命”等文革图景的反例,一些学者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足以证伪“文化大革命扼杀文化”的假设。在农村,样板戏的演出晚于城市,自1968年兴起,随样板戏电影的普及而衰落。通过精简配器,戏曲交响作品走向基层,提供了令农民耳目一新的经典剧目,在最广阔的乡村践行了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教化,其影响经久不衰。高默波聚焦江西波阳一个村庄的变迁,发现样板戏演出是高家村初次接触剧场性的集体观演。农村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是生产队为样板戏演出提供资金,并为参演农民记工分,调动了基层文艺骨干的积极性。83沙垚在对陕西皮影戏的田野调研中发现,以盈利为目的、非样板戏的其他剧目虽也由人民公社自筹经费,但按照副业收入来管理分配。84由县文化部门进行文化统筹,突出样板戏,兼顾民间形式,既限制了乡村讲唱形式中最卖座的“三俗”内容,又照顾到农民艺人开展文艺劳动的积极性。以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制作单位,农民自行对演出资金和场地进行物质调配,这些文化活动既因地制宜又自给自足。张丽军以山东寿光庄户剧团为案例,对地县以下地区样板戏的群众参与做了问卷统计,发现突出样板戏的农民文艺在人民公社条件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活跃度。85
对文革历史负面材料的过度曝光,固然是为了反复证实“历史终结论”和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但正视文革的种种教训,也是此刻这个“历史终结论”终结之时,我们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何摆脱“毛的最后的革命”的总体图景,还原文革“派性”的真相并分析其流变?我发现,样板戏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政治研究中的“派性”考察打开思路。纵观样板戏研究,它虽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文革研究,但从文艺领域向政治领域突破的尝试从未中断。近来学界对文革时期的文化生产的讨论已拓展至视听层面。彭丽君聆听了1974年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张贴前后录制的粤剧版《杜鹃山》,指出其中西混编的配乐形式是一种乌托邦运动破灭之际的离经叛道。86在文革时期样板戏的评论文章中,“洋为中用”被反覆强调,而“后文革”的样板戏研究者往往忘却了这一点。实际上,七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洋乐器和外语的热潮,“中国比任何国家有更多的李斯特”87。有识之士如John Winzenburg 注意到四十年代犹太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编创之音乐剧《孟姜女》的“京剧交响化”与样板戏的相似之处。88Barbara Mittler 也在对《智取威虎山》戏曲交响化的分析中注意到观演中样板戏的模式化与多元性并存的开放性。89这些研究反过来证明,粤剧《杜鹃山》的音乐特点并非地方特性,恰恰是地方剧团学习样板戏的结果,是“革命/礼乐”向地方传播的案例。
因此,“边缘”、“民间”、“地方”、“异端思潮”的所谓“文革主体”在“反叛”中央的过程中创造出新形式,这类说法值得商榷。反观文革的“派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从下列三个方面决定了“派性”这个流动的象征形式:一是“约定俗成”,例如文革中的群众对多元性(革命)和正统性(礼乐)的好恶,具体体现在血统、阶级、亲疏、专业和阅历等方面的倾向性;二是文革运动中的主体性,例如群众在前述之革命/礼乐的倾向中做出的“敌友”区分(文革中的“逍遥派”通常主观上拒绝判断“敌友”,躲避或放弃自己的倾向性);三是“敌友”区分后进行的实践,例如“隔离”或“联合”这两种做法。造反派组织的参与者自身往往在出身等方面更多元,易倾向于在运动中推动“联合”,取消身分差异,不断“拉人”。而保守派组织的参与者,通常在出身上更单一,他们倾向于在运动中不断辨别“差异”,唯身分论,采取“隔离”手段,不断“踢人”。总之,“派性”是流动的象征形式,它不是固定的判断,其实践随文化革命的形势不断变化。因此,样板戏的目标,正是要宣传“隔离”、“联合”的辩证法,教育群众如何吸取“武斗”带来的“血的教训”(如《杜鹃山》中一段核心唱段的标题),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不断辨别“敌友”。
以上,将“文化”、“政治”两方面的研究聚集起来,我们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规定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舞台规定性。文革中,在舞台艺术领域,“文化革命派”拒绝塑造无差别的群众,通过颠倒旧的等级,让无产阶级的“新君子”登台。在那个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只要样板戏演出每天进行,旧人成为新人,“底包”、“角儿”互换,“龙套”争做“主角”,知识分子下乡劳动,工农兵上大学⋯⋯凡此种种,并非封建等级制的回潮或“政治名分”的争夺战90 ,而是群众在毛泽东所确立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规定情境”91中的“即兴发挥”。
对于招致“武斗”的“派性”,具体某派或某人,出于各自的透视单点,体验到对立面的“人格化力量”之时,也极易深陷其中,无法对眼前的“再现”做出反思。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后悔史学”是对“再现”的不断回放。“派性”至今连绵不绝,甚至影响了对“派性”的研究。对此,这里不展开论述。概言之,“派性”顽强的生命力来自群众运动本身,“派性”的历史恰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从来不是在任何“无菌实验室”中培养出来的,一切“新人”的诞生都须“经风雨,见世面”92。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台上再现“新人”易,台下“新”人难。文化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克服技术局限和理论难题,更在于将资产阶级“新青年”教育成社会主义“新人”。安舟认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技术官僚”这一文化的“新阶级”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家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93在中国,文化的“新阶级”被毛泽东称作“意识形态工作者”。“意识形态工作者”这个术语来自毛泽东在1968年8月31日给《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加的按语。这个群体包括了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工作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在内。五四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者”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是“自在的阶级”,将来自古代或外国的要素运用于新文化的创造。94延安时期,他们是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同路人,保持了其“自在”的状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各类协会和单位中,他们成为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三名三高”,最顶端是“文化官僚”。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群体被塑造为具有“无产阶级认同”的“自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文革时期,对“意识形态工作者”中的“新人”的塑造是建构无产阶级文化的题中之义。文革研究者邹谠认为,宏观的政治转型需要微观的理论调整和文化策略的辅助,以“组织社会进程和心理进程的样板”。95在微观层面,文化大革命以相对而言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广阔深远的“新”人效果。结合党史、单位体制、家庭关系等等,才能看清文化知识分子从被动到主动、从被迫到自觉、从客体到主体的心路历程。文革前的“文化官僚”被“打倒”,艺术工作者的个人使命感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这二者的同一化,催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这一群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文化知识分子被作为“技术官僚”的科技知识分子边缘化;“文化官僚”虽回到原地,却失去了“十七年”中掌控的政治资本。“技术官僚”这一新阶级的诞生,是文革结束后新生的政治精英与文革前的旧知识精英的合流而成的。96安舟强调新、旧精英,文化、政治资本等方方面面的“一分为二”;相较而言,我更侧重于文化革命的总体性中,文化与政治的“合二为一”,关注在“新”人的、广义的文革剧场中,流变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艰难地达成均势。
概言之,作为礼乐革命最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指向“花部”的“联合体”,那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一种未完成的革命礼乐。
注释
69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 年。
70 相关讨论参见文浩、魏昂德、安戈、安舟和吴一庆:〈2016 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派性问题圆桌讨论会的报告〉,《记忆》,第 189 期,2017 年 7 月 31 日。
71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72 林伟然:《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威斯康星州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96 年,第 9 页。
73 王绍光、阳敏:《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南风窗》,2007 年第 2 期。全文见 http://www.cuhk.edu.hk/gpa/wang_fi les/Publist.htm,2017/3/31 查阅。
74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5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31: 463-519. 又见安舟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
76 “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这一政治形式即“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三联书店,2008 年,第 40 页。
77 Andrew Walder. Tan Lifu: A “Reactionary”Red Guar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0 (Dec., 2004), pp.965-988.
78 王绍光:《“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开放时代》,2013 年第 1 期。
79 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0 Roderick MacFarquhar. “Mao’s Last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45, No.1 (Oct., 1966), pp.112-124.
81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Free Press, 1999, p.302.
82 宋嘉俳:《思想革命还是制度革命?——以〈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为中心》,“1970 年代思想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2017 年 2 月 4 日。
83 高默波著,章少泉等译:《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4 沙垚、梁君健:《农村文艺实践的再思考:以人民公社时期关中地区的皮影戏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 年第 3 期。
85 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
86 彭丽君著,李祖乔译:《复制的艺术: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及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
87 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江青同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第 501 页。
88 John Winzenburg. Musical-Dramatic Experimentation in Yangbanxi: A Case for Precedence in The Great Wall, see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Ed by Paul Cla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89 Barbara Mittler.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90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页。
91 规定情境(given situation),是 20 世纪舞台电影表演的主要流派苏联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剧表导演术语。指作家在剧本中为人物活动所规定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以及艺术家们在二度创作中对剧本和演出所做的大量内容补充。《演员自我修养》一书解释了规定情境的含义。规定情境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两个方面。外部规定情境就是剧本的事实、事件,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各种外因的根据。内部规定情境是演员创作所要依据的一切主观条件的概括,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各种内因的根据。外部情境与内部情境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92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 年 11 月 29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93 安舟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
9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8 页。
95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转引自 Cliff 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Basic Books, 1973. pp.216-220。
96 安舟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
推荐阅读
《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导论丨样板的成型:从“礼乐革命”到“革命礼乐”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张晴滟。来源:《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张晴滟。来源:《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