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2 月,一篇题为《对新冠疫情的结构性反思》的三万字长文在朋友圈传播。文章论及了疫情中的谣言、官僚制度和国家主义。令人瞩目的是,作者是三位 00 后,来自「Philosophia 哲学社」(以下简称哲学社)—— 一个中学生为主导的哲学社团。
知乎上,一位哲学社成员的留言或许可以视作他们的画像:「在该社的组织成分中,出身帝都上海等资源堆砌圈的文化沙龙爱好者、出国党学生占成员的主体,这一点就足以解释社内浓厚国际主义的文化氛围和左翼青年的圈层生态。」
18 岁的丁白则像其中的异类:他出生、成长于北京,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从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他回到了安徽省的老家,继续高中生涯。曾为「资源堆砌圈」中一员的丁白,在被迫接受「下沉」的生活经验后,是否更新了对理论和现实的思考?又是否能给哲学社注入新鲜的、异质的能量?
今年 7 月,我和刚高考完的丁白第一次通话。两个月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他即将入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哲学是他的兴趣,但他希望以社会计算为主业,在本科毕业后继续出国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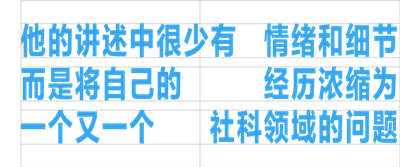
丁白的思辨能力远远盖过情感表达。他的讲述中很少有情绪和细节,而是将自己的经历浓缩为一个又一个社科领域的问题。即便是谈及高三遭遇的一次重大精神危机时,他也迅速略过了「情绪」的部分,将其阐释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和真诚」的伦理学问题。
不过 18 岁,丁白已经经历了观念的流变:他曾受马克思主义的感召,怀揣激情和理想;而在穿越公私领域的大小风暴后,如今他自称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试图以更落地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
交谈的六个半小时中,丁白收到了四次母亲发来的微信,要求他晚上和亲戚一同吃饭。「不想去。」他轻声地抱怨。只有这时,我才会意识到,他还是一位刚刚成年的男孩。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父母都来自安徽,大学考到了北京,就一直留在北京发展。我爸爸是安全工程师,妈妈是个体创业者,两个舅舅都是工科领域的学者。我出生成长于北京,也把北京视为家乡,但我没有北京户口。
我读的是海淀的小学,当时海淀的教育没这两年「内卷」的那么厉害,但竞争已经很激烈了。那时候我们得上两种培训班,一种是外部的培训机构,一种是各个中学内部的「占坑班」。如果能进入这个班并最终通过考试,就能被点招到这所学校。我也报过占坑班,但最后是通过「推优」去的北大附中 —— 推优的是市三好,或者连拿几年区三好。
不管哪种升学方式,最看重的都是奥数。我大概是从一二年级就学奥数了,学到六年级,每周末去学三个小时,也拿过相关的奖项。但我现在觉得,小学奥数对我的数学思维没有什么帮助,它太强调直觉和技巧,缺乏对分析技能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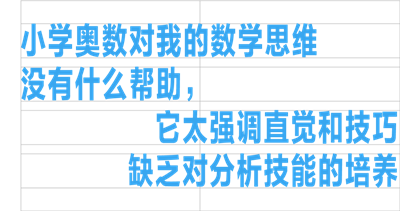
进入北大附中后,我的学习就变得松懈了。尽管会有外部压力,但我很少给自己施压。我每天傍晚 5 点到家,作业很少,7 点之前就学完了。很清闲,甚至有点混日子。那时我参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艺术社团 —— 民乐社、音乐剧社等等。每周五天,其中三天下午 3 点后是社团活动,一天是选修课。选修课有数十种选择,常常需要要抢课,像热门的「犯罪心理学」就很难抢到。
北大附中很重视尊严教育。(比如)我们俩坐在一块儿,互相是不知道彼此排名的。学校的游学项目也都是靠自己申请,并不按照排名来。像北大附中现在在做《防性骚扰手册》,同样在强调对女性尊严的保护。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的氛围是相对自由的、开放与平等的,我很少感受到流动感。也许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会形成另一种身份认同: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在北大附中,我们彼此知道对方老家在哪里,但很少会区分有没有户口。我觉得我和其他同学就是一个圈子的。直到初三要走,我才发现,年级里回原籍读高中的少之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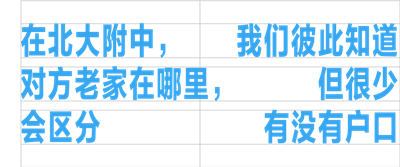
当然,从我小学开始,我妈也多次试图帮我在北京落户。不过中间涉及复杂的程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那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我没办法在北京高考。
很多家庭因此会送孩子出国,美国本科四年的开销得两三百万,经济压力很大。争取奖学金也有风险:万一在国际学校读了三年,没申到奖学金怎么办?后来也断了这条路。大概初一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得回老家读高中。
在我看来,近年来对户籍问题的处理较为粗暴,因此带来了很多制度障碍。比如为了解决流动人口,一个农民工到北京务工,把他所在的乡改成镇,这个农民工就算城市人口了,表面上解决了他的市民权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我以前算是个文艺少年,还给文学杂志投过稿。但写到后来会发现,写作往往容易流于言辞的「制造」,比如为了写出一种风格而刻意地营造陌生感。最后写作完全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东西 —— 满足我想象的欲望,把我思考的力量扩张到语言中 —— 但我的语言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这种体验最终会消解我写作的价值感。
小时候我住在奥运村旁边,小学后面是一个批发市场,很多外来个体户在那里做生意。也接触过安徽老乡的农民工 —— 我们不用农民工这个词,用新工人 —— 能在空间上感受到明显的区隔,比如他们会住在地下室。
电视上,我能看到很多关于新工人的新闻,搬迁、讨薪或者各种社区管理问题。在媒体形象上,新工人被描述为有肢体力量,但不爱卫生、素质不高的人群。现在回看,这非常不利于他们获得应有的公民权利。
 新工人们常被划分为一种特定的群体,游离在社会主流人群之外。
新工人们常被划分为一种特定的群体,游离在社会主流人群之外。
逢年过节时,一堆亲戚出来吃饭,我就会听说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有人提到一位老家的亲戚,被中介雇去湖北恩施打工,然后工伤了。中介和公司都不愿意承担赔偿。在场多数人都表示同情,但也会有人谴责受害者:这个人怎么工作都不会找?
我想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应该赔偿吗?那时候我对现状满怀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会萌生一种道德情感 —— 这是追究「什么是正义」的原始动力。
也是因为有过一点对城中村的观察,当时我写了篇小说,写一个在城中村的边缘艺术家。为了积累更多的素材,我看了李强老师编的一本《城市社会学》,收录了学生的田野调查作业,算是从那时对社会学萌生了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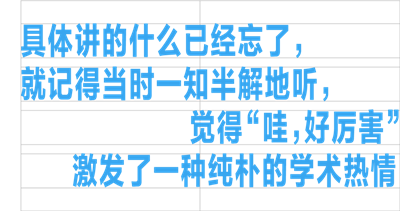
北大附中离海淀区的很多大学都不远,我和朋友去北大蹭过一堂关于宋史研究的课。具体讲的什么已经忘了,就记得当时一知半解地听,觉得「哇,好厉害」,激发了一种纯朴的学术热情。
初中的政治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不用政治课本,给我们讲 Gregory Mankiw 的《经济学原理》,也谈公共层面的正义问题:四个人在船上,其中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被吃掉了,回到英国,法官应该怎么宣判?这是从行为功利原则引出的问题。
从小到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规范性判断,却没有被阐明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来自父母的干涉。比如小孩子都会经历的: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被子叠成方块?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看一些书,希望讲出一套道理。最后发现这样一件日常小事,背后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完全无关于他人利益的私人生活存在善恶吗?习俗本身具有道德价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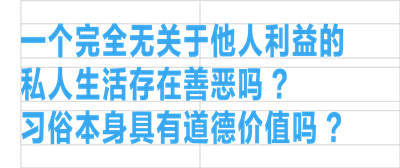
所以我最初接触哲学,都是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这种相对落地的,到了高中才意识到,应该去读更基础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
但哲学也会给我带来一定的无价值感。我发现它的成果不够显化,难以与社会需求直接对接。同时,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精细化趋向,也给当时的我带来失落 —— 当然,我承认它是学科成熟化的特征,从而影响认知科学等具体知识的建立。
因此,尽管哲学是我的兴趣,我更倾向于以社科领域为主业。2012 年前后,我开始上博客和微博,当时中国互联网洋溢着自由主义的风气。在公知还没有被污名化之前,他们都很愿意在网络上发言,我也习得了他们的问题意识。
本科阶段我希望巩固自己需要的数理基础,可能偏向网络科学领域。这种落地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会让我在价值的层面更有信心一些。

我老家在安徽省枞阳县,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之一。以前我就回去过两三次,那时觉得老家特别好,「生活在别处」嘛,在老家没有紧张感,像度假一样。
中考前,我回到老家,准备中考。为了保留县中的生源,安徽的城市中学很少在县内招生。我考不到足够高的名次,就留在了县中。县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整个学校数千人,其中很多人也许从幼儿园起就是同学,两个高中同学之间大概率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
实话说,回到老家后,我对老家的滤镜被打破了。县城拥有一种严密的秩序,比如公务员是十分吃香的,其次是教师,然后是小零售商和工人。有老师会在课上和我们说,学计算机和金融比其他理工科好,理工科优于人文学科;北京上海比南京广州好,南京广州又比合肥好。我经常怀疑,他自己是否相信这些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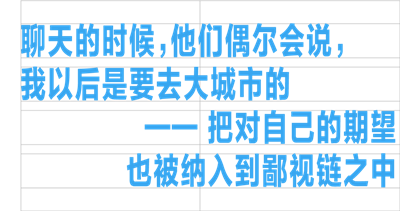
有些成绩好的同学同样会很傲慢,热衷于同学间的恶性竞争。聊天的时候,他们偶尔会说,我以后是要去大城市的 —— 把对自己的期望也被纳入到鄙视链之中。农村小孩会被这些同学称为「下面来的」。
中国县城是农村与城市间的过渡带,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县城的人感到无可适从,想要出去。
安徽有很多高考大县,但并不意味着这里很有文化氛围。拿我们县来说,图书馆不怎么开放,书店里卖的都是教辅。整个县城只有一两家电影院,放的是爆米花电影。偶尔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县里的广播电视局组织的,一般是黄梅戏相关,有时候是名人返乡的讲座。
县城很少有哲学爱好者。我的高中同学里有历史爱好者,但没有哲学爱好者。原因嘛,大家可能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学科,是侃大山,聊生死,像诗人一样自杀。像我妈算好一些的,她会觉得哲学是周国平谈尼采。有一个朋友受我影响,对哲学有了解,但他仍不会自称是哲学爱好者 —— 前者的心态是「哲学是挺重要的知识,我要补一补」,后者则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我生活的问题,我哪怕不做哲学,也要时时去思考它。
 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地区,县城也承载着许多信息资源上的冲突。
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地区,县城也承载着许多信息资源上的冲突。
哲学社是以哲学普及为己任的,但想要覆盖几线城市或县城中的孩子也很难。他们很难看到哲学社的文章,并且这些文章是对某一个具体流派、具体问题的综述;而要对哲学产生兴趣,往往要通过翻阅教科书、修读课程来了解全貌。所以哲学社能为初步的哲学爱好者指引方向,却较难让对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成为哲学爱好者 ——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在我的观察中,高中时的同学会将生活分成两部分,学习和娱乐 —— 学习是应付高考,娱乐是获取快感。但其实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是那些能带来价值感的事。这在县城是相对缺失的。
人总是有把自己普遍化的趋向,有时候我会因周围的环境而苦恼:为什么一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议题,在其他人的眼里轻如鸿毛呢?
这也许是很多「流动儿童」(共有)的经验:原来的社交圈被切断了,又无法融入新的群体。

我们高中也是「衡水模式」。衡水这种精密的管理模式正在向全国的县中扩散,用流行的词语来说就是「内卷」: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很难做大蛋糕,却要走向内部的恶性竞争。
但这种扩散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就以我所处的县中来说,升学情况或是不稳定,或是呈现了下降趋势。这是近年来热门的议题之一,也引起过我的思考:为什么县城教育和大城市间的差距被扩大、显化了呢?
你知道豆瓣上的「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吧?一些自称「小镇做题家」的朋友到大学后,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广阔的认知视野。我觉得县城和大城市的教育差异,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资源的差异。

小学时为了升学,我学过参加过剑桥英语的等级考。在北大附中,我的英语水平十分糟糕,但升高中后,我的英语却相对很好。初中我还修了一门叫做「电影音乐欣赏」的选修课,老师让我们用大学慕课(MOOC)看相关课程。那时我就掌握了大学慕课这个工具。回到安徽后,我仍然会用慕课自学很多大学课程,校内这么做的人应该是很少的。后来,我也上网课,网课可以选择 1.25 倍速、1.5 倍速,上课效率提高不少。
刚进高三,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身边的同学们好像一下子都变了,从早上 6 点半到晚上 10 点半,除了中午睡个觉,一直都在学习。课上不学新东西了,就是不停复习,不停回顾,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价值感。学习效率也变得极低,大脑处于混沌的状态。其实关于高考,我很早就想清楚了:为高考做的准备,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提高我的知识水平,它的意义在于,在规则下为每个人取得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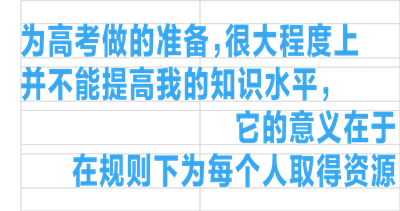
但想清楚了不代表就不苦恼了。有些人认为高考数学(成绩)从 140 分提到 145 分,他的数学水平就提高了,这种人一定很快乐。我们可以从经典的「快乐机」实验展开想象:如果你进入一个体验机,每天做什么都是快乐的,那你会进入这个机器吗?
对我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个体需要的不仅仅是快乐感,更是对「快乐感真实」的确证。换到价值层面也很近似,高考在知识上对我的价值许诺被打破了,我会因此感到无奈。
我不想再待在学校了,就说服了家长,并让家长说服了学校。整个高三我都在家学习,只是偶尔去学校考考试。和高一相比,这让我的成绩退步不少,但我并不大后悔。

高二下学期,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初中同学转发了一条推送,是哲学社联合举办的 L.G.B.T.Q 平权日活动。我又翻到了他们之前写的哲学普及和社会评论,觉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我通过这个同学认识了哲学社的成员,发了几篇我写过的文章后,就通过了。
我一直觉得哲学不能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过程。它需要各种交流会议,需要各种期刊评介,这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处,才能更新自己。
哲学社最早是北师实验的校内社团,后来逐渐向外拓展,早期是一个很强的关系网络。拿我的情况举例,我同学加入了哲学社,我看到了,才有机会加入。最初的很多社团成员都来自北京,有一些在上海和深圳,其余省份都是少数。很多现在都在国外读书。
哲学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流派,有相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像我这样的温和派。但总体上,左翼是大家的共识。
 Johann Friedrich Greuter,《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Socrates and his students),1590年。
Johann Friedrich Greuter,《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Socrates and his students),1590年。
哲学社是我高三生涯中的一项慰藉。睡前半小时,我都会看看哲学社的群,也插几句话。大家都挺忙,有时候发一条消息,过了 15 分钟才有人回。
我在哲学社上发的几篇文章,大多都是旧文,其中有两篇是即写即发的:一篇是月考考完了去看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花两三个小时写的影评;另一篇是在寒假写的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哲学普及文章。
因为一些原因,前任社长最近退出了哲学社。之后,哲学社一直都没有选举新社长,而是成立了一个行政群,由不同人负责不同职能。靠的不再是个人,而是制度。一些朋友认为,哲学社不需要社长了 —— 它现在的运行效率确实很高。
除供稿之外,我还在哲学社的议会群里。比如出台审稿制度这样的重大决策,就会由议会群来做。

和哲学社中很多成员一样,我也曾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思潮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因为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未经反思的、甚至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一些左翼学者会以审视的态度描述它们,比如「父权制」「消费主义」—— 这是个问题化的过程。
然而,这些概念在迷人的同时,也具有危险性:它可能过于空泛,甚至沦为话术。拿父权制举例,在上世纪 80 年代,Bonnie Fox 就梳理出了它的三种定义。在谈论这些概念时,我们可能忽视那些具身性的体验,忽视问题的复杂和差异性。
现在我更愿意定义自己是「左翼自由主义」。举个例子,在新工人问题上,激进左翼的思考方式是,是什么社会结构造成了压迫(「压迫」是他们的习惯用词),造成了异化,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左翼自由主义的思路则是,为什么新工人们应当获得公民权,为什么分配正义原则要求在收入上对他们倾斜 —— 最后,我们如何去改变现状。在我看来,左翼自由主义是在思考复杂的正当性。

我们这一代没有前人的集体记忆。老一辈的学者能从经历溯源,比如自由主义学者之所谓成为自由主义者,是因为对文革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对政治性的集体行动 PTSD。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的成长经验和主流社会议题的距离还是挺远的。我们在相对去政治化的教育体系下长大,而主流的议题曾是民主、社会正义、公民意识,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经历。
说到集体记忆,疫情应该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集体记忆。疫情对我观念的影响特别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会强调活动自由的不可侵犯性,但在实践上遇到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 它的确导致了感染人数的增长,加剧了不安全性。一种是活动自由的价值,一种是公共安全和稳定的价值,两种价值我们怎么权衡?在紧急状态下怎么处理权利克减的问题?政府如何去落实一个公共卫生方案?现在我更倾向于从对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许这是更实用主义的立场。
现在很多人自称「政治性抑郁」。我并不喜欢这个词,这些朋友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可能过于糟糕: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立场,选取世界的某个特定侧面,来描述现状 —— 可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种想象复杂。假如没有抑郁症的病理表现,我不赞成一个人把自己日常的抑郁情绪视为谈资:这可能意味着你缺乏充足的情绪调节能力。
用罗曼 · 罗兰那句很鸡汤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李弘。来源: T 中文版。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李弘。来源: T 中文版。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