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越》是“新工人乐团”的“第一张”正式专辑。
“新工人乐团”,前身为“新工人艺术团”“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乐团的历史,探察成立近20年来乐团创作实践的“常”与“变”,进而理解《从头越》的“内”与“外”。

一
2002年劳动节,“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成立,2003年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为劳动者歌唱》(2007)《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2009)。2009年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此后出版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2010)《就这么办》(2011)《反拐》(2012)《家在哪里》(2013)《与机器跳舞的人》(2014)《劳动与尊严——新工人艺术团呐喊十年精选专辑》(2014)、《挣脱枷锁》(2015)《红五月》(2017)。2018年,新工人艺术团巡演期间,“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在那儿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互助’的新路线,团队名字由之前的‘新工人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乐团’,更专注于音乐发声。”[i]2019年劳动节,“新工人乐团”发行EP数字专辑《新工人》[ii]。2019年9月,出版专辑《从头越》。
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艺术团”,再到“新工人乐团”,歌者的初衷未改,其作品一以贯之立足新工人群体的劳动与生活状态,以劳动者的视角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应。不过,名称的改变,亦表明歌者在不同阶段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团体的期许和定位有不同侧重。下文将涉及“乐团”不同时期专辑中的作品,为方便论述,笔者采用“新工人歌者”,而不用更广为人知的“新工人艺术团”,也不用或许较多听众还未熟知的“新工人乐团”,来称呼这一秉持“为劳动者歌唱”宗旨的团体。[iii]
梳理新工人歌者创作发展的脉络,2009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是具有“承前启后”意味的一张专辑。
专辑同名曲目《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的主歌部分,以并举对比的形式,唱出了新工人群体之“世界”和“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九平方,从早到晚不停地奔忙。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地到工厂 打出一片天地来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长长的流水线,赶货加班加点不知疲倦。付出了青春泪水和血汗,省吃俭用寄钱回家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钢筋混泥土,高楼大街桥梁都是我们双手来建。脏苦累活儿没日没夜地干,顺利拿到血汗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孤单和寂寞,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城市灯火辉煌我心空空荡荡,梦里时常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
我们的世界是别人的冷眼,冷漠与偏见我习以为常。我一不偷二不抢心底坦荡荡,顶天立地做人要有做人的尊严。
我们的世界是烈酒和乡愁,天南地北四海皆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好汉需要三个来帮。
我们的世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疯狂的机器它轰隆隆地响。工伤事故职业病痛苦和绝望,平安健康有保障是我们的梦想 。
我们的世界是矮矮的村庄,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学习歌唱。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总理说的话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我们的梦想是同一个梦想。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创造一个新天地是我们的梦想。
…………
“我们的世界”,即新工人的生活现实,包括生活空间(狭小的九平方)、工作场所(长长的流水线、钢筋混泥土)、心理世界(孤单和寂寞)、现实境遇(别人的冷眼、冷漠与偏见)、社会交往(烈酒和乡愁,天南地北四海皆朋友)、子女生活和教育场所(矮矮的村庄)等方面。
“我们的梦想”,则包括个人理想(打出一片天地来)、生活责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现实诉求(顺利拿到血汗钱、平安健康有保障)、个人尊严(顶天立地)、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等。这些,说是“梦想”,不若说是应得的权利和保障,本应是“我们的世界”之内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描绘新工人群体生活和工作的现实,他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诉求,以及两者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尚且存在的落差,是新工人歌者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一内容,是其“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宗旨的体现,《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这首歌,以及这张专辑,较为集中全面地呈现了这一内容和宗旨。
在《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之后次年发行的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中,“新工人艺术团”的名字取代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与“打工青年”相比,“新工人”[iv]这一名称,更符合这一群体生活和工作的实际,更明确地表达出了他们的诉求,也彰显出一种更主动积极、自我赋权的主体。这一主体不再是“北漂的过客”,亦不是以实现个人成功为目标的城市追梦者,而是希望依靠社会主义基本理念,“团结起来,建立集体”(《怎么办》,收入2011年《就这么办》专辑),对现实有所能动性实践的主体。在此后几张专辑中,新工人歌者表现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思考,他们要把漂浮在空中的“劳动的价值”“放进我们的手掌”(《放进我们的手掌》,收入2010年《放进我们的手掌》专辑),“唱大地、山川和人民”(《我的吉他会唱歌》,收入2011年《就这么办》专辑),并将目光投向处于同一境地的劳动者,将改变现实境遇的希望寄托在劳动者自身。如果说,此前漫漫冬夜里“疑惑着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的“我”从送来一车煤的老乡身上“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煤》,收入2007年《为劳动者歌唱》专辑),还是朴素的情感萌发,维权“根据地”六里桥(《六里桥》,收入2007年《为劳动者歌唱》专辑)、团结起来讨工钱的工地现场(《团结一心讨工钱》,收入2004年《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携起手来,共同拼凑我们的理想”的社区姐妹行(《社区姐妹行之歌》,收入2009年《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专辑)还只是自发组织的维权形式的话,那么在《就这么办》专辑中,“团结起来,建立集体”的呼喊,则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梦想”之间,构建了一个桥梁。在2017年的专辑《红五月》中,更是唱出了“火红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场”的宣言。
或许可以说,着眼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理想”之间的落差和裂隙,召唤能够弥合两者的新主体,是贯穿新工人歌者创作实践的主线。
二
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时隔十年,更名为“新工人乐团”的歌者,出版专辑《从头越》。
如果说,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艺术团”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主体观的确立,那么,从“新工人艺术团”,到“更专注于音乐发声”的“新工人乐团”,有什么转变和发展呢?[A1]
专辑十首歌曲,除了旧曲新编的《想起那一年》,有9首新作品。
新专辑自然还是延续了此前一以贯之的“为劳动者歌唱”的主题。2016年加入新工人歌者团体、此前做过12年矿工的新成员路亮创作演唱的《矿工兄弟》和《这个冬天》,用新工人歌者常用且娴熟的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的方式,连带出对新工人整体境遇的思考。《矿工兄弟》是一首饱含切身情感,又有着自觉追问、意味复杂的作品。歌曲首先描绘了“矿工兄弟”工作的“典型环境”(“上班下班两头都不见那太阳”)、做出的贡献(主观上看似没有远大理想,工作源自对家庭的责任,实际在为社会默默奉献),继而发出了对“皮带运送着那青春的梦,用乌金做成了铁饭碗”的矿工兄弟之伟大还是渺小的追问。歌曲有追问,有呐喊,源自自身经历的情深意重,亦有对劳动者的价值和意义的重申,具有打动人心、促人思考的力量。《这个冬天》,则以“冬天的皮村”这一“典型环境”入手,描绘了歌者由寒冷的天气和萧索的环境而生发出的孤寂与追问。
两首许多创作演唱的歌曲值得注意。《冬天里的游击队员》是较为典型的“多式”歌曲,延续《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收入2013年《家在哪里》专辑)、《红五月》(收入2017年《红五月》专辑)的“革命摇滚”风格,运用“游击队员”、“野火”“春风”等典型意象的组合,营造一种近乎革命浪漫主义氛围。至于《新十月》,或许更适合做本张专辑的名字,“带着五月后的分裂,继续上路到达新的十月”的宣言,显然是对《红五月》的延续。歌曲糅合古诗和现代派式的语句,在古典与现代的断裂与冲突中,呈现一种革命和爱情交织,幻灭与理想并存的场景。
在《从头越》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出新工人歌者一直在吟唱、召唤的那个主体:他背井离乡,他饱受辛苦;他满怀理想,他遭遇不公;他胸怀劳动者的自豪,他相信双手换来的美好;他背负生活的冷遇,他期望现实终究会改变;他思念乡村的父母亲人,他感动于城市工友的温暖;他也许会陷入孤独寂寞冷,但他相信团结带来的力量;他面对一时的遭遇感到困扰和愤怒,但他并不失却乐观昂扬的心态;他有时面对现实迷失彷徨,但他有志为了未来披荆斩棘;他是具体的一个个工友,他也是被歌唱赋权的“新工人”。
此外,专辑也有几首歌曲,似乎呈现出一种较为“宽泛”,或曰“曲折”的抒情,即是说,与此前专辑相比,几首歌曲不是直接呈现新工人群体“典型”的生活场景,更近似某种较为“普遍性”的抒情。《我从未将自己找到》《西藏南路》《报春晖》《起风的夜》,单从歌曲内容本身看,抒情主体近乎一个“旅者”面对生活某个情境而产生的情感抒发或自我追问。以老诗人蔡其矫的诗作为词的《距离》,则是更为含蓄朦胧的抒情。
对于这种抒情方式,排除专辑出版方面的考量,笔者更愿意结合歌曲文本内外的语境去理解。
在2013年出版的《家在哪里》专辑文案中,新工人歌者如是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智慧和血汗,创造了中国的繁荣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却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的城市,迷失在城乡之间。
城市待不下的原因容易理解。回不去的乡村的原因,如该专辑第一首歌《春天 故乡》中所唱:“想到了故乡,故乡在远方,干枯的河床,衰败的村庄。从乡村到城市,找不到安身的地方,脚步越来越慌张,内心越来越迷茫。”乡村不是现成的故乡,而也在现代性进程中被改变了本来的面目。城市的发展依赖乡村,却拒斥建设它的新工人群体。
近年来,过度追求城市化的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明显地显露,夸张的房价、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种种,使得一些城市开始主动寻求疏解之道。同时,乡村建设多点开花,发展呈蓬勃之势。新工人歌者亦积极介入这一实践。他们的足迹,除了城市、学校、工地,也有计划地走向了广阔的乡村。2014年,新工人歌者开启“大地民谣巡演”活动,成员组队自驾车,走遍全国演出。刚刚结束的2019年巡演,历时45天,行程万余公里,深入十几个省市的村庄演出28场。或许,在这样的巡演中,新工人歌者进一步发现了乡村的活力,乡村的力道,将建设乡村,进而回馈城市的“城乡文化互助”作为解决城乡发展、突破某些瓶颈问题的路径。有学者将这一实践称为“文化的万里长征”:“新工人群体来自农村,心系家乡,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将成为振兴新乡村的主要力量。振兴乡村不只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振兴,因为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谣是一次文化的万里长征。”[v]
在深入乡村的实践中,新工人的主体性也获得了扩展,新时代的“新工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当代工人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力图返回乡村,重建乡村,并力图在此一实践过程中构建“新文化”的探索者。
如果说,“新工人”这一命名,现实依据是他们“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vi],其隐含的实践场域是“城市”。那么,深入乡村的行动,拓展了他们实践的场域,追求一种建设乡村、反馈城市的“城乡文化互助”路径。实践场域的拓展,使得新工人歌者将新工人群体的未来,放到对城乡、工农问题的探究中。抒情的“宽泛”,或许是这种实践维度拓宽的反映。
当然,熟悉新工人歌者的听众,依然能从这些看似抒情“宽泛”或“普遍性”的歌曲中听出他们一以贯之的风格。《我从未将自己找到》由工友胡小海作词、孙恒作曲、演唱,孙恒的方言演绎,以及与歌词的迷惑、追问内容不相匹配的铿锵有力的曲调,似乎容易听出孙恒此前的作品《我的吉他会唱歌》乃至《团结一心讨工钱》的愤怒却不失坚定信念的声音。而从《西藏南路》,似乎亦可以听出演唱者姜国良的《蒲公英》(收入2013年《家在哪里》专辑)中对“家在哪里”的追问,以及《放进我们的手掌》中对“劳动的价值在风中飘着”的不平之音。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相隔不到半年的EP专辑《新工人》专辑,这张被许多提醒应视为《从头越》“序曲”[vii]的专辑的四首歌曲[viii],则一如此前,呈现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梦想”,以及其间的落差。可以说,《从头越》是一张有“常”亦有“变”的专辑。其“常”,即“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宗旨,为新工人命运而歌的“初心”;其“变”,是新的实践场域带来的“乐团”的工作重心和歌曲抒情方式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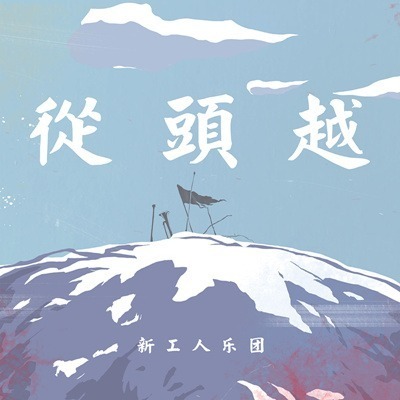
三
需指出的是,《从头越》的音乐风格有较为明显的变化,音乐编配似乎更加“复杂”,技术更加“考究”。在此前的创作中,作品或采用铿锵有力的节奏,曲调朗朗上口,唱出劳动者的宣言;或以简单乐器伴奏,方言或白话讲新工人群体的生活、工作、情感,娓娓道来;或以轻快诙谐的调子,表达乐观积极的情绪。在这些作品中,音乐更大程度是为歌词服务的。歌词直白、通俗、清晰,易于在工地、学校、乡村等不同场所演出时,为不同听众所接受乃至传唱。
而在《从头越》中,音乐较为突出,掩盖了歌词。同时,歌词的修辞性也更强,总体上呈现出音乐凸显,歌词不易直接、准确把握的特点。而在笔者看来,是歌词,而非音乐,更能典型地标识出新工人歌者创作演唱的特点。作为新工人歌者的较长时间听众,笔者听完专辑的第一时间,甚至一度有专辑的“可听性”远不如之前的感觉。
相比笔者粗浅的听觉经验整理,刘雅芳更准确且专业地指出《从头越》的特点:“即便是民谣吉他配唱的歌曲,和弦的声响也比较高(以前编曲类似的歌曲,人声会略微突出)。专辑整体的音场在后制上更重视音响效果,带来的第一层听觉感受基本上与以往定义的民谣摇滚、抒情摇滚专辑差别并没有太大。”她亦提出疑问:“我不晓得已经习惯以往“艺术团”音乐风格的听友、歌友是否能习惯这样的变化,这个转变也透露着乐团编制摇滚乐专辑的能力颇为游刃有余。” [ix]如前所说,笔者初听的时候,确实有不习惯的感觉。[x]当然,这或许是新工人歌者“更专注于音乐发声”诉求的体现,也或许与歌者“曲折”的抒情方式相关。
进一步说,作为不习惯这样变化的听众,笔者更愿意理解为:新工人歌者,以及更多的新工人文化的实践者,在守护、推广新工人文化的成果的实践中,在走遍大地探究“城乡文化互助”路径的旅程中,积累了太多的经验,这些经验,亦需要相应的艺术形式。但在艺术形式层面,或许还没有现成的、充足的储备,去充分呈现这些经验。经验溢出了形式,所以带来了一时的不适。
这种不适,或许也是一种新的创造的前奏。
近20年来,新工人歌者正是将经验——包括新工人群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自己创造新工人文化的实践经验——灌注到独特的音乐形式之中,创作出百余首别具一格的歌曲,这些歌曲又通过其传播、接受,推动了新的经验的生成。那么,有理由期待,“更专注于音乐发声”的歌者,也将如此前那样,以“经验”推动“形式”的创造,进而呈现一种更为鲜活、更具生产性的“经验”。
漫漫雄关漫漫歌,而今迈步“从头越”。
注释:
[i] 参见《从头越》专辑文案。
[ii] EP专辑,即迷你专辑(extended play),即相比一般至少收录十首歌的正式专辑,收录歌曲较少的专辑。参见百度百科词条“迷你专辑”。《新工人》即是一张有4首歌的EP专辑,故而笔者将《从头越》而非《新工人》视为“新工人乐团”的第一张正式专辑。
[iii] 2019年11月24日,笔者就新专辑文案中“更专注于音乐发声”这一定位的含义,请教新工人歌者的骨干之一、“新工人乐团”团长许多,据他介绍,此前“艺术团”的演出,不仅包括音乐,也包括相声、舞蹈等多种文艺形式,“更专注于音乐发声”,是指团体更专注于音乐方面的实践。这也提醒笔者,“打工青年艺术团”“新工人艺术团”,不仅是创作歌曲、出版专辑的“歌(乐)手”,亦是多种形式的新工人文艺、新工人文化的实践者。不过,鉴于本文探讨范围,主要是出版的13张音乐专辑,所以用“新工人歌者”这一称呼。对于更广范围的“新工人文艺”及“新工人文化”实践将另行撰文探讨。
[iv] 关于“新工人”名称的由来、依据、含义以及其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参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和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
[v] 参见《大地民谣全国巡演即将启程 打造文化万里长征》,“朝闻天下”网,2017-10-28。
[vi]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和崛起》,第11页。
[vii] 参见刘雅芳:《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注释20:“许多叮咛,要把《新工人》EP作为《从头越》专辑的序曲来一起听。”,《热风学术(网刊)》第14期。
[viii] 四首歌曲分别是:《一路有你》(路亮)《过客》(孙恒)《皮村北路》(姜国良)《不干啦》(许多)。
[ix] 刘雅芳:《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x] 刘雅芳对此风格持宽容的态度,她指出,“很神奇的是,这样的摇滚声响质地也让专辑的调性洋溢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青春感。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刚”,尤其许多、路亮的歌声音域是属于比较高亢的,但是也仍有姜国良温厚的歌声,还有孙恒更为深沉的说与唱。”而且,“……对于一支面对着内外情势的转变而想要透过新的尝试而继续走下去的乐队,我们应该支持并对他们的革新给予意见,因为还会有下一张专辑,还会有下一次演唱会。”参见刘雅芳:《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崔柯。本文原载于《热风学术(网刊)》第15期,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崔柯。本文原载于《热风学术(网刊)》第15期,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