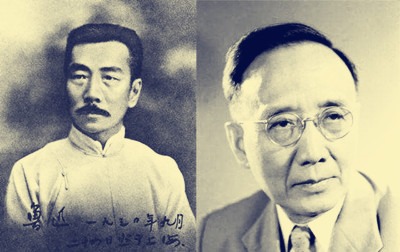
1932年,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鲁迅这里说到的在上海“遇见文豪们笔尖的围剿”,熟知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章节的“革命文学”论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这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由于是论战,参加者发表的一些文章都带有一些火气,甚至率意扣帽子。比方说,以杜荃的署名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用尖酸的语言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fascist(法西斯蒂)”。而且,由于是论战,很多人的文章是以笔名发表的。称鲁迅为“封建余孽”的杜荃就是一个笔名。
关于鲁迅这段话,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者们,在笔名的考证上却留下一个空白:即对“杜荃”没有像对“石厚生”后面加上一括号注明是成仿吾一样也加上一个括号注明是何许人也——《全集》其他涉及到“杜荃”的也同样如此。这个问题就留给了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了。
据陈早春考证:杜荃就是郭沫若;定稿小组:真人不好露相。
鲁迅的《三闲集》,收录在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中,该卷的责任编辑是陈早春。陈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与冯雪峰交往很密切,对《鲁迅全集》的编辑也是了解的,所以对“杜荃”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要真正找出这个人是谁,却还要下一番功夫。
经过多方考证,陈早春做到了这一点。在1977年中央决定由胡乔木、林默涵来领导并主持《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时,他就拿出了考证的结果:杜荃是当年创造社的首脑郭沫若。因此,他在关于鲁迅这段文字中的“封建余孽”的注释中,在杜荃后加上一个括号,写明“郭沫若”。
但是,陈早春的考证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陈早春告诉我:
我在第四卷第一稿上,也就是初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却被划掉了;第二稿我还注明,仍然被划掉了。在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上,我仍然坚持写上,但都如同以前一样,还是被划掉了(2003年11月8日电话采访陈早春记录)。
虽然陈早春没有多谈及被划掉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定稿小组不让杜荃的真人“露相”,大致还不是对陈早春的考证结果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这个考证的结果是郭沫若。
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是学术范畴的事,但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他与文坛一些人交往的复杂的情况等等,对《全集》进行编辑、注释,有时候不免要牵涉到一些重大的人和事。正因为如此,不管是1958年版还是1981版的《全集》编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1958年版就不说了,就1981年版来说,早在1977年,中央就决定由胡乔木挂帅,林默涵披挂上阵,主持这一工作(后因乔木忙于其他工作,便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这年12月初,林默涵就和《全集》编辑一起就注释、整理与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以及注释体例等拟出了条例。在这个条例中特别要求:“注释中遇到的一些较重要或较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有了这项规定,编辑在遇有一些较重要的注条,经反复讨论拟就初稿后,或由林默涵审定,或由林转请胡乔木或其他有关同志审定。
陈早春的考证结果,显然是属于应该“严格掌握分寸”的范畴之列。定稿小组当然要慎重考虑了——五次将这个注释划掉,自然是这种慎重的结果。
另外,当时让定稿小组为难的是,郭沫若对此有“记不起来了”的答复。当然,郭沫若的答复,不是他看到了陈早春的考证结果,而是他在回答当年与他一同参与论战的创造社另一名元老冯乃超的询问时说的。冯乃超将郭的答复写在了《鲁迅与创造社》一文中,此文在1978年第二辑的《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想来编辑领导小组不得不作这样的考虑:既然郭沫若本人已经“记不起来了”,陈早春的考证结果再正确,恐怕也不宜在注释上体现,只好割爱了。
陈早春无奈上书,胡乔木、周扬定夺。
一条辛辛苦苦考证出来的注释被五次划掉,陈早春心有不甘。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考虑,他对定稿小组的负责人申述自己的意见。负责人无奈,只好对他说:你打一个报告吧,我们考虑一下,或者给你转送上面来定。于是,陈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写成了下面这个长达4000字的报告:
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小组:
鲁迅在《三闲集》、《二心集》中,多次提到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引用了其中一些带刺激性的话。杜荃是谁?五八年全集本及近来的征求意见本,均未注明,我拟指明他为郭沫若,并在初稿中这样作了,但未予通过。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既是个资料问题,也许还是个政治问题,是需要慎重考虑,但我觉得,似还有提请领导重新酌夺的必要。
照我看来,杜荃即郭沫若,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实。
杜荃是不是郭沫若,鲁迅肚里是雪亮的。他在一九三○年写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在引杜荃的文章时,特别点名出自《创造月刊》的“东京通信”。经查杜文发表情况,作者和《创造月刊》编者均未说明或者暗示文稿寄自东京。这只能说明,鲁迅是在做有意的暗示,希望读者明了其人。这一暗示,读者是不难领悟的。当时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几乎都在国内,只有郭沫若避居东京。所以,这里暗示的虽然只是该文作者所处的地方,而读者却可连带想到身居这地方的作者。当然,那时在东京而又参加国内革命文学论争的也许不只郭一人,但除了身负盛名如郭沫若之外,鲁迅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暗示的。如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直呼其名了。他说:“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众所周知,一九三四年“以前”郭与鲁迅直接或间接交绥的文字,都署本名或常见的笔名,所谓化名,当为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杜荃。
杜荃即郭沫若,鲁迅生前还向冯雪峰说过。一九七三年,冯告知了笔者,并连带说到了鲁迅一九三二年写的一首七绝《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尽,春兰秋菊不同时。”冯说,这首诗是题送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的。沈虽然为鲁迅出过书,但无甚交情,不便直接找鲁迅题字,只好转求冯。鲁迅本来不太乐意,但经冯请托,也就应允了。诗写好之后,冯不懂其含义,当即问鲁迅。鲁迅说:“‘东云’就是日本;‘春兰秋菊不同时’,我与郭沫若不是搞不到一块吧,杜荃骂我的话,我怎能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也有过向郭沫若组稿的念头,但立即就打消了”。冯还说,这诗谈及郭沫若,可能因为沈与郭关系不错,沈的书局为郭出过书。
冯在这里所说的情况,该是可信的,因为鲁迅曾笔之于书,当可宣之于口,何况这样联系到鲁迅的作品谈其创作时的感慨,任何编造巧手,也不可能做到如此细密无缝的。
杜荃即郭沫若,与创造社有过关系的张资平也是这样认定的。一九三○年五月,张资平为了回答鲁迅《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在《洛甫》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答黄棘氏》(按黄棘为鲁迅笔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要正告黄棘氏,不要不谈书而尽去“援中国的老例”啊。假如英文教师同时对外国史有研究,当然可以教外国史;国文先生对伦理有素养,也未尝不可担任伦理学。“二重反革命”、“封建的余孽”、“不得志的fascist”(见麦克昂氏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尚可转化为革命文学先锋!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黄棘氏知道否?
这里我们可以略去其他的文字不谈,能说明问题的是:杜荃—麦克昂,麦克昂—郭沫若,所以杜荃—郭沫若。张资平这时已经脱离了创造社,他在这里点名杜荃的身份,是不是对郭沫若的栽诬?据知张资平与后期的创造社虽然闹翻了,但他与前期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交情并未绝决,所以栽诬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张资平的文章来看,他引郭沫若的话,是想借重郭的名气,以加强他对鲁迅的攻势。
郭沫若对于这件事,虽然一直没有承认,但事实上是默认了的。一九三○年初,他读了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颇深感慨。写了《“眼中钉”》一文。其中说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时说:“关于鲁迅呢,我只间接的引用过他的一句话,便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见《文艺论集》中的《天才与教育》)而且我还认识他的并不是‘傲语’”。同文又就此“坦白地招认”说:“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成、郭又何尝开诚布公?……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两段文字,读者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前者所举出的事实,看不出对鲁迅有什么不满,更说不上是什么“封建遗习”。作者这样落笔,只能是默认了一桩未曾举出的与这一断语铢两悉称的事实。一九七七年十月,冯乃超特为杜荃事询问郭沫若,他既未看肯定,也未否定,只是说“记不起来了”(见《新文学史料》第一辑《鲁迅与创造社》)。如果杜荃是郭沫若,这句话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的文章不是兴到之笔,时过境迁就会忘掉了;如果杜荃不是郭沫若,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的文章成为举世瞩目的公案,自己不是是非中人,怎能“记不起来”呢?惟一可能的解释,是作者的默认。
杜荃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之外,还有一篇《读<中国封建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作者无疑与创造社是有关系的。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列主义有过一番研究,是当时舆论界的先驱者,不是创造社的一般追随者,而是中坚分子。他的文笔极其圆熟老练,在二十年代能达到如此水平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大手笔。而从文字风格看,则与郭沫若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我不想罗列那些显而易见的特点,只想说及如下一点似乎就够了。郭沫若文章独有的“正字”的习惯,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一部甚长的文章中,就出现了六次之多。“正字”的极端是扣字眼,而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都是靠扣字眼建立的。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杜荃文章中的观点,看是否与郭沫若的相吻合。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有这样一段话:
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没缘……在未读这篇随感录(按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前我的鲁迅观是:
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
这是杜荃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说的话,而郭沫若在“以前”的二月写的《留声机的回音》中就这样说过了:
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但是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我相信他们是不自觉,或者有一部分是觉悟而未彻底。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这里好像是杜荃抄袭郭沫若的观点,然而过不了多久,郭沫若又转而抄袭杜荃的观点了。
自从杜荃对鲁迅与语丝社(他与郭都将他们扯到一块了评价)的看法由“不革命”升到“反革命”甚至“二重反革命”之后,郭沫若对语丝派的看法也跟着改变了:他们“却胶固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堡垒”,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见《文学革命之回顾》,作于一九三○年一月)
其实,这里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因为杜荃就是郭沫若。
如果我们再看看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惊叹:杜荃与郭沫若何其相似乃尔!
一、同时研究同一问题,同一进度。
杜荃说:“目前(按指一九二九年)我正准备研究这个事项(按指中国古代社会),……我自己目前的题目是中国的氏族社会向奴隶制更向封建制的转移,已经研究得稍有头绪,是正想向封建社会突进的”。郭沫若说:“一九二九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为了要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见《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记》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已写完并编?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
二、同一研究目的,针对同一社会问题。
杜荃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的旧人们有一句口头禅,便是‘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课目应该有一道是:要来使他们看看中国的情形究竟同也不同!”郭沫若也在一九二九年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三、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研究方法。
杜荃说:“marx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序上说:‘大体上亚细亚(即氏族社会),古典的(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及近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体制之发展的期望。’这四种是必经的阶段。据笔者的研究,周代正和希腊罗马之古代相同,是奴隶制,当时的所谓‘封建诸侯’其实多是自然发生的王国。中国的真正的统一在秦始皇廿六年兼并天下划一制度权衡文书以后!!!”而郭沫若这时写就、一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恰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论证了我国古代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他对于各个社会阶段的划分,也与杜荃一样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如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周代才开始奴隶制时代等。
这里只能荤荤举其大端,其他相同的地方还不少,如对于禹,两人都认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国的先住民族”。而所根据的资料都是齐侯×的“处禹之都”一语。当然,后面这句话还可值得斟酌,因为郭沫若在写《夏禹的问题》时,还补充了齐侯×一条材料,但这是一九三○年二月写的,如果杜荃的文章不是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而是写于这时,他也是有可能作这个补充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荃与郭沫若的相似,不是一般学术观点上的“英雄所见略同”。这是同他阅历、同一世界观、同一思想水平、同一学术修养,而又在同期达到同一建树。这不是孪生儿般相似,而是同一魂魄、同一身手、同一五官的同一人。
基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我认为杜荃即郭沫若,鲁迅的话还是可信的。冯雪峰的话是可信的,张资平的话也是可信的,然后最可信的还是郭沫若的文章。俗话说:“文如其人”,见其文即可识别其人,何况我们所引郭的文章,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文字风格。
我们说杜荃即郭沫若,这是实事求是,是尊重历史,尊重我们注释工作者的基本原则。而且这样实话实说,对我们所尊敬的人未必有什么损害。郭沫若的一生,已盖棺论定,虽然他骂鲁迅的这一文章,不是根据事理,但纵观郭老一生,他对鲁迅是奉为旗帜般地尊敬的,一时的失言,不影响他的名世之论,更不影响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其实这也是无需也不能“讳”的,郭沫若与鲁迅都曾以“笔墨相讥”。这是大家熟知的文坛掌故,不限于上述的一例。
鉴于以上理由,特此建议:
一、 在鲁迅著作中凡是牵涉到杜荃时,当著名他即郭沫若。
二、转请郭沫若全集编辑委员会,将上面说到的杜荃两篇文章收入集中。
不知领导以为如何,候盼指示。
《鲁迅全集》第四卷责任编辑
陈早春
1979.8.3
陈早春的这个报告,转悠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在1980年3月13日由林默涵送给“周扬同志并乔木同志”审定。林默涵在附上的信中写道:
鲁迅《三闲集》序言中,讲到有人骂他是“封建余孽”、“棒喝主义者”,这是指《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的话。杜荃何人?过去的注释都未讲明。现在鲁编室负责此书注释的同志,根据各种材料,认为杜荃就是郭老,看来他的看法是可信的。但是否注明,我们没有把握。先将陈早春同志给定稿小组的信送阅,请你们考虑应当如何办?盼即示知。
前面说过,胡乔木具体负责《全集》的审定工作,周扬并没有参与此事。林默涵把报告送给胡乔木即可,为什么还要加上周扬的名字?原因除了周扬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周扬此时是“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林默涵也是编委)。林默涵认为,既然陈早春在报告中提出将其结论告知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就更有必要让周扬或郭著编委会来认定。如果周扬同他一样认为是“可信”的话,这一考证结果,对正在编辑中的《郭沫若全集》也大有益处,将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和《读<中国封建史>》两文收入《郭沫若全集》也是应该的。
3月17日,周扬批示说:
和郭著编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一下,我看可以注明。请乔木同志酌示。
同一天,胡乔木批示说:
同意周扬同志和陈早春同志的意见。
至此,已经接近于定稿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中,加上了这条注释。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看到陈早春的报告后,却提出了异议,由此又引出了周扬和李一氓之间的信函往来。
王廷芳:结论还有待于继续探讨李一氓:从历史的高度看待注释
在周扬将陈早春的考证结果交“郭著编委的同志共同研究”的时候,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看到了这一报告。他虽然承认陈的考证是一家之说,但仍认为结论还有待于继续探讨;而且,他对陈文中的行文也颇有意见。为此,他给周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周扬同志:
最近我才看到你和乔木同志对林默涵同志关于“杜荃就是郭沫若”的请示的批件及附件。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向你反映一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是郭老85岁的生日。冯乃超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声韵同志、朱洁夫同志和他的夫人杨英华同志上午一起来郭老家中看望郭老,祝贺生日。郭老虽在病中,当天精神很好,很高兴,谈了很多话,当场赠送了新出版的《沫若诗词选》给他们两夫妇,并亲笔将他们两夫妇的名字题到了书的扉页上,留做纪念。在谈话将要结束时,冯乃超问郭老在1928年至1929年之间,是否用过杜荃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对杜荃这个名字,乃超同志说了几遍郭老还是听不懂,乃超同志就在一张纸上写了杜荃两个字,郭老才听明白,他拿着这个名字,沉思了很久说,我当时用过麦克昂、杜×、易坎人等笔名,记不起来用过杜荃这个笔名。除了杜×以外,我记不得再用过杜什么的笔名。乃超同志看到郭老已经很累了,就起身告辞。他并且把一本铅印本载有杜荃文章的32开本的什么资料留给了我,让我趁郭老精神好时给郭老看看,再帮助回忆一下这件事。我按照乃超同志的意见,很快就把这两篇文章给郭老看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是全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摘要。郭老看后对我说:《中国封建社会史》这篇文章和我当时的观点很相似。《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章是摘要,不知全文是什么样,从这个摘要中,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你想法找一份全文来看看。但我记不得用过杜荃这个笔名,你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乃超同志吧。我按照郭老的指示及时的告诉了冯乃超同志。同时托阿英同志的女婿吴泰昌代找一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全文,不久郭老病情加重,吴泰昌同志也未找到该文,事情就放下了。
冯乃超同志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的《鲁迅与创造社》一文中扼要提到了此事。使我十分惊讶的是,《鲁迅全集》第四卷的责任编辑陈早春同志,在他给《鲁迅全集定稿小组》的报告中,说郭老“记不起来了”是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进而说郭老“记不起来了”这句话不可信。这篇文章是郭老写的,郭老也不可能“记不起来了”,不是郭老写的,郭老也不可能“记不起来了”。他结论就是这篇文章就是你郭沫若写的,你郭沫若在扯谎。同时你郭沫若自己也默认了。我觉得陈早春同志这种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对一位85岁高龄重病在身的人,对将近50年前的一件事,连“记不起来了”都不允许,未免太过分,太苛求了。
我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不是郭老写的,还可以进一步的考证和讨论。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这两篇文章是郭老写的,他绝对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不承认这件事。我还清楚的记得,五十年代楼适夷同志他们编辑《沫若文集》时,有人建议他把《创造十年》中的《发端》一文删去,他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并为此写了那样一条很重要的注,坚持把这篇文章保留了下来。为什么二十年后他的态度会完全改变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陈早春同志也承认,这篇文章即便就是他写的,也不会“影响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更不可能使鲁迅先生更加伟大。
陈早春同志的考证,作为一家之言,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的方法和态度,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对鲁迅的话是作为证据来看待的,然而不难看出,鲁迅的那些话,实属猜断,也算一种考证吧!考证毕竟是考证,考证不是证明。只有证明才能定论。要证明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①发现原稿;②走访当事人,故人的话要听,在世人的话,也要听。特别是与此事有关的健在的老一辈同志的话,就更应该听。但是陈早春同志在这方面缺少积极行动。还有,陈早春同志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对郭老也欠尊敬,这里就不多说了。
只要方法、态度对头,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
因此,我建议:
一、鲁迅全集要注明杜荃即是郭沫若,应加上“据考证”或者“据××人考证”为好。
二、现在的情况下,郭老的全集不收这两篇文章。
三、热切的希望成仿吾、李一氓、阳翰笙、冯乃超、李初梨同志帮助回忆一下这件事,尽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四、再进一步在刊物中讨论这一问题,看其他人能否提供一些新的情况。
以上意见,如有不当之处,望指示。
顺致
敬礼!
王廷芳
六月十九日(80年)
王廷芳信中以郭老对待《发端》一文的态度为例,说明郭沫若所说的“记不起来了”并不如陈早春所言,是对问题的“回避”。这一事例的确是存在的。
1931年,郭沫若写成了回顾、总结创造社历史的长文《创造十年》。文中虽然谈及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但对鲁迅的态度尚属平和。不料,1931年7月20日,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他在评述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其功过时,指出创造社等在这次运动中所产生某些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演讲中并对某些创造社的成员提出了批评。郭沫若读到后,对鲁迅的批评感到不满,便在已完成的《创造十年》一文中加上了一篇《发端》。文中再次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鲁迅,称鲁迅为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
到了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沫若全集》时,当时担任郭沫若秘书的王戎笙主张不收《发端》一文。但是,郭沫若坚持要收,并为此发了脾气。王廷芳告诉我:
郭老一般是不发脾气的,但当王戎笙同志向他建议删去这篇文章时,郭老却发了脾气。他说,这是历史嘛,一定要收。后来,还是收进了书,郭老并特意写了一个注释(2003年8月8日采访王廷芳记录)。
郭沫若在注中写道:
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些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王廷芳的这一意见虽然很有道理,但仅凭这一点却不足以颠覆陈早春扎实的结论。不过,周扬对此倒也很重视。他是否与成仿吾、阳翰笙、冯乃超、李初梨(均为郭著编委)等人商量过,没有材料证实,但他的确与李一氓(亦为郭著编委)商谈过这个问题。有李一氓致周扬的信为证:
周扬同志:
关于“杜荃”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郭老,他生前未承认,冯乃超不自己说是或不是,而去问郭老,就把事情弄复杂了。
鲁研的意见应接收,两文均应编入郭集。事情又会引起一些议论。现已成为笔战,说不好听的话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当时1928-1930这时期的“左”倾怎么看,从历史唯物论而言,自有它的必然性,也可以说当时“不错”,事后看来是错了。在大革命失败的前提条件下,而这些同志都是失败的参加者,幸存下来,不左一下反而不会进账。难道逃避或消沉,只有在左一下之后,才转为沉着应战。我不想多说,我是说不要怕写“法西斯”而矢口否认,说杜荃不是郭老反而不好。说杜即郭,是实事求是,进而为之申辩,说那时左一下并无不可,这是历史,这是斗争。不过现在新月派,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都一概翻身,反而要把郭老打下去,怪就怪在这里。只差为王天陵、张道藩之流说好话了!
敬礼
李一氓
八月四日
李一氓信中提到的“新月派,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是指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派别新月社。该社在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这一派基本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在政治上主张“英国式的民主”,“好政府主义”,在文学上则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至于“正人君子”的称谓,语出《大同晚报》。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大约周扬很赞成李一氓的意见,也主张从历史的高度对鲁迅与郭沫若的“笔墨相讥”来认识。因此,他希望李一氓把信中的观点加以发挥,写出一篇文章来论述,以期引起人们的探讨,达到王廷芳所说的“进一步在刊物上讨论这一问题”的目的。但是,李一氓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您的意思是好的。但您知道我现在的注意力放在中联工作上,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对付这件事。虽然这个问题总是一个问题,总得端出来,可一发表,必然万箭起(齐)发,我可招架不起。暂时,偶尔写几行给您,聊以快意而已。乞谅。顺颂著安!
李一氓
九月四日
李一氓虽然不接受周扬的建议,但仍认为“这个问题总是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陈早春的考证固然很正确,应该接受,但是另一种现象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即“有些研究鲁迅的人,忽略了研究鲁迅与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的关系,忽略了研究《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这些鲁迅杂文的精粹所在”,一味地纠缠于争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忽略了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这场争论。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谈到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时说:“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不在于他写了几篇讽刺创造社的文章,而在于他站在中国劳动人民一边,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贡献了他的智慧。”这正是从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结论。
这里,李一氓没有谈到对郭沫若及创造社的看法。不过,联系他给周扬的信,套用他对鲁迅的评价,说他会这样地评价郭沫若恐怕也是实事求是的:“郭沫若之所以为郭沫若,不在于他写了几篇讽刺鲁迅的文章,而在于他站在中国劳动人民一边,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贡献了他的智慧。”
当然,这是引申出来的题外话,不去说他了。与本文相关的内容是: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认可了陈早春的考证,那两篇署名“杜荃”的文章,收进了《郭沫若全集》。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徐庆全。来源:《纵横》。责任编辑:培天壤)
(作者:徐庆全。来源:《纵横》。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