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1913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来。卡斯帕罗夫给《启蒙》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词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见。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它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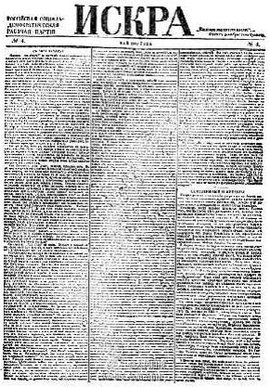 火星报
火星报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在就不同了: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杂志和报纸说来,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伊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意思仍然不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伊里奇在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的问题,90年代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列宁怎样把以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题须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左翼文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地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达里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他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语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某个成语或语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是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列宁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写过很多工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一封信中谈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相互“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写得很好”。于是,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是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来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以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造神说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写过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一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康·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有点象Deus ex 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娜·康·注)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职权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意见。维拉·伊万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她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她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时,也象同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和作者。我流放在乌法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1900年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把工人的通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1902年6月16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怎么办
怎么办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它叫作万尼亚。——娜·康·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人给《火星报》写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给巴布什金写了一封信(我们很了解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学习过,还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课的小组):“我们对您有个请求。请您到图书馆为我们找一份《俄国财富》杂志(从去年12月份起)。因为有个名叫达顿诺夫的在那份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使人愤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写成不懂得什么团结、没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尔宁在该杂志上反驳了达顿诺夫。达顿诺夫又写了一篇更使人愤懑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杂志就宣布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讨论。请您读读这些文章(如果需要,请您买所需的几期《俄国财富》杂志,我们付钱),并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短评(我在信中写的是‘短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评’。——娜·康·注),尽可能多收集一些实际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添了‘或《曙光》杂志’几个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学杂志上能够出现工人的文章。——娜·康·注)或《曙光》杂志上发表一篇比较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娜·康·注)写的反驳这种无稽之谈的文章。”巴布什金写了这篇反驳文章,编入作为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的附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护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物色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由于当时的条件,做这个工作,要进行复杂的通信,建立秘密联系,当时工人通讯员和作者一共只有几个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人数有了增长,这使伊里奇无比地高兴。现在,工人通讯员已经是一支强大有力的大军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源:《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责任编辑:卢淼)
(作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来源:《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