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伊朗的第三号人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负责人苏莱曼尼被美军用无人机刺杀,国际局势一时紧张,不少媒体甚至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1月6日,无数伊朗群众涌上首都德黑兰街头,参加苏莱曼尼的追悼会,进行反美的民族主义大示威[1];但是,短短的几天后,因为军方失误击毁载有80余名伊朗乘客的乌克兰客机,近万名伊朗人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矛头直指伊朗政府,他们撕毁苏莱曼尼的肖像,要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台。剧情反转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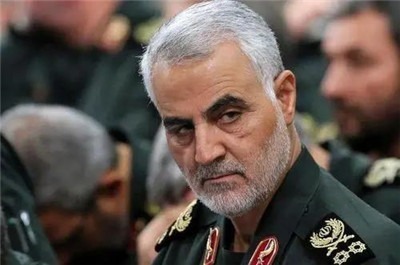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
伊朗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中东地区的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作为世界上唯二的政教合一国家之一,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与今日这个世俗化的世界似乎格格不入[2],以《古兰经》的法理来治理社会,总让人不自觉地联系起落后保守的封建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伊朗出兵进攻IS,帮助叙列亚政府军打击反对派,对中东地区频频输出革命;伊核问题更是困扰世界十几年,主要大国围绕着它明争暗斗。在国内,伊朗近几年经常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走上街头的民众呼吁民主自由,抗议政府,要求最高领袖下台,颜色革命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但这种示威却又往往很快消退。不断摩擦出来的火花又快速熄灭,这些局部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朗政教合一的体制为何能延续近40年,它未来将走向何处?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我们必须深入到伊朗内部的社会结构中去。
1、失败的世俗化改革与伊斯兰革命
1921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巴列维发动政变,推翻了半殖民地的封建恺加王朝,强力推进了伊朗的统一和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大刀阔斧地实行世俗化、民族化和西化的改革。196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了“ 白色革命”,依照美国的蓝图来进行伊朗的农业与工业改革,例如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森林水源收归国有、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势力等措施。另外,还签下了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犯罪不受伊朗法庭审判,而是交给美国处理。白色革命后,伊朗创造了GDP连续十年(1962-1972)平均年增长11.5%的伊朗奇迹。紧接着在1973-1975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国际油价暴涨,GDP增速更是分别达到了14%,30%,42%。整个巴列维王室陶醉在经济繁荣的狂欢当中。
 伊朗“白色革命”
伊朗“白色革命”
繁荣的表象下面,社会阶级矛盾却在积累。
在土地改革中获得收益的农民不足1/2,即使是分到了土地的绝大多数家庭,由于土地贫瘠,面积狭小,“到1971年绝大多数村民的经济地位并不好于土地改革实施之前。”[3]巴列维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和农业公司,农民获得的土地又重新失去,生产积极性低下,大多数合作社和农业公司也最终停办[4],大量农民陷入贫困境地,他们被迫涌入城市。由于伊朗城市的工业发展不足以吸纳如此多的的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的农民只能从事不稳定,收入很低的服务业工作,他们成为城市贫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使得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不满日益加剧,这为宗教影响的扩大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以巨额石油收入为后盾,依托政府巨额投资支撑的工业化,使得伊朗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政府主导投资,私人资产阶级更多地处于辅助性的角色,他们受到国有官僚垄断资本和外资的双重挤压,自身地位和力量较为弱小;伊朗的工人人数从1956年的81万人猛增至160万人,产业工人虽然地位低下,收入微薄,但依然比在农村时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所以他们在大多数时间对政权的不满程度较低。
传统的巴扎[5]商人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白色革命期间,巴列维扶植和发展大量现代工业,进口大量商品,传统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巴列维国王鼓励全国范围内开办连锁超市和商店,代替巴扎。1975年经济衰退,为转移各阶层对政府的不满,巴列维发动了一场针对巴扎的反对牟取暴利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约有8000名巴扎商人入狱, 2万名巴扎商人被流放, 2万家店铺被迫关闭。广大巴扎商人对国王的专制极为不满,一位店主向美国记者透露,“如果我们任其自然,国王将会摧毁我们,银行将会接管我们的业务,大商店将夺走我们的生计,政府将会保护国家机构而打倒我们。”[6]由于伊朗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展,巴扎商人的经济力量依然很强大,在20世纪70年代,巴扎依然控制着当时伊朗国内贸易的2/3和对外贸易的1/3,这个群体成为了反对巴列维政权的坚定力量。
宗教界也对巴列维王朝也极为不满。作为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朗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也非比寻常。自16世纪中叶以来,什叶派欧莱玛已经成为伊朗的一个重要阶层和政治力量。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和财政资源,他们长期控制着伊朗的教育和司法。但是在白色革命中的土地改革后,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被政府分给佃农。国王发动深入农村的知识分子,削减神学院的数目,否定欧莱玛的教育和司法权力。由于巴列维王朝这一系列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宗教界和政府逐步走向对立。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真正获益的便是以国王巴列维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王巴列维以“巴列维基金会”的名义控制了一百零五家工矿企业,合股经营了十七家银行和保险公司,控制了二十四家豪华饭店,垄断了旅游业、商业中心以及附属的水泥和钢铁制造业。他们垄断了伊朗教科书的出版,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获得一笔数目不菲的利润。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形势,占全国人口1%的皇室贵族、大官僚和大资本家霸占着全国80%的财富[7]。
 巴列维王室
巴列维王室
在所有的阶级中,宗教界人士,巴扎商人,农村贫农,城市贫民,都是在这场白色革命中受到损失的群体,他们人数庞大,社会基础深厚,在意识形态领袖的影响巨大;私人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相比农民又有一定的改善,他们对现有政权的不满程度较低,这两个阶级人数较少,在伊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较小;唯一获得收益的只有以巴列维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掌握着党政军大权,但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阶级的支持。在反对政权的阶级中,宗教界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伊朗穆斯林占到人数的95%,历史上什叶派欧莱玛对伊朗政治多次产生巨大影响,在70年代末伊朗国内有8万家清真寺庙和近20万欧莱玛,他们通过宗教系统能够高效地组织伊朗民众,尤其是组织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现政权的阶级便自然以宗教界作为领导,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也就自然成为了政权反对派的领袖。对此,霍梅尼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深刻:“宗教、清真寺和毛拉是人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他们之所以转向我们,是因为他们感到,现代化和那种被大肆吹嘘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宁。”[8]
从1977年开始,国内的游行示威便此起彼伏。到了1979年,伊朗的局势已经失控,巴列维出逃国外,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返回伊朗。君主政体被推翻,伊斯兰革命获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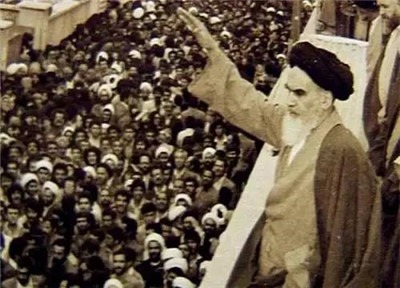 霍梅尼回到伊朗
霍梅尼回到伊朗
2、神权政治与共和国的结合体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士集团,通过清理异己的力量,逐步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建立起来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这套政教合一的体制建立在“教法学家治国”的原则之上,这套原则认为,真主是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绝对主宰。真主委任精通伊斯兰法典、明辨是非的教法学家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表,掌管国家,以保障所有的社会事务不偏离伊斯兰教的准则。在教法学家治国的原则基础之上,才是所谓的“共和国”,人民通过选举议员参与立法,通过选举总统代替人民管理国家。
形式上,伊朗的国家首脑是总统,但实际上最高领袖才是真正的当家人。在行政权力方面,最高领袖可以监督总统的选举、任命和罢免。伊朗的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但是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得到最高领袖的认可才能进行候选。在立法权方面,伊斯兰议会可以根据民主原则制定法案,但是法案生效必须要得到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批准,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核实议会的方案是否违反伊斯兰教法,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由最高领袖任命,也即,最高领袖事实上能决定方案能否通过;在司法方面,由最高领袖任命司法总监,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最高领袖也掌握了司法权。
在军权方面,最高领袖是伊朗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和其它国家不同,伊朗的武装力量除了正规的陆海空军外,还有一支宗教武装,这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由霍梅尼在1979年革命胜利后,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武装合并建成,革命卫队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以及导弹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由最高领袖领导,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保证对革命卫队的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虽然人数只有正规军的1/3,但是却占据了国防预算的2/3,武器装备水平明显优于正规军。国内的镇压职能和国外的输出革命均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完成。通过这一系列方式,最高领袖牢牢把握了军权。
由于霍梅尼的巨大威望,伊朗的第一任最高领袖由霍梅尼担任,在霍梅尼之后,最高领袖由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形式上看,这一方式对最高领袖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实际上,专家委员会的候选人要由宪法监督委员会中的6名教法学家来审查,而这六名教法学家又由最高领袖任命。最终,最高领袖能事实上指认下一届的最高领袖。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专家委员会选举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至今已有三十余年[9]。
在最高领袖之外,伊朗的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人民投票普选产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议员也由伊朗人民普选产生,任期四年。就这样,民主共和的躯体和“教法学家治国”的大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任何一套制度,都是一定环境下社会各阶级博弈的结果。伊朗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也是1979年革命胜利后各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共同对抗巴列维王朝时,各个阶级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当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不同阶级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自由资产阶级希望建立一个类似西方的世俗化的民主共和政体,但是他们力量太弱小,很快就失败了。教士集团的期望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因为他们在当时代表着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巴列维王国时期,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农生存艰难,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陷入了困境。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士集团许诺,一个由教法集团领导,按照真主意志运行的伊斯兰国家能够实现《古兰经》中平等的理想社会,在浓厚的伊斯兰传统下,农民和城市贫民必然选择教士集团,而非倡导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
当然,口头许诺的效力是短暂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要得到支持,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必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革命胜利之后,伊朗新政权没收了巴列维王室、权贵、原政府高官、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和庄园,实施了以国有化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宣布将全国的私营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收归国有,后又对交通运输、电信、公用事业和工矿企业实施国有化,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体系。同时,教士集团利用没收的这些财产,建立上百家庞大的宗教基金会,基金会负责给伊朗低收入人群、烈士家庭、农民、没有监护者的家庭、残障人士提供经济帮助。依托国营经济体系和宗教基金会,1980年代,伊斯兰共和国把重心放在了农村和贫困人口上,试图修正“白色革命”时期对农村的摧毁式掠夺带来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让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享受到基本的供电和自来水服务,基于资源的国有化分配,医疗和教育保障覆盖了几乎所有人口,伊朗国民的识字率和平均寿命都得到了极大提高[10]。起源于80年代的许多保证社会公平的经济制度延续了数十年,如油品、基本食品及日常消费品的价格补贴。这些针对底层的一系列政策,围绕这些政策建立起的教士集团、贫农和城市贫民的联盟是伊斯兰共和国这套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的根基。宗教统治的现实土壤,不存在于资产阶级之中,也不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而存在于这些农民和城市贫民之中。
3、私有化改革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但是,这种联盟并非能永久维持。
伊朗的教士集团,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垄断资本集团,这个垄断集团,以宗教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截至2017年,伊朗的国营和半国营经济的比重高达80%,这些财富,事实上被大的教士家族控制[11]。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执政的时候曾经披露,伊朗国家60%的财富由伊朗300个教士家族掌控[12]。由教士集团把控的宗教基金会,独立于伊朗经济体系之外,它控制了40%的非石油经济,雇佣40万劳动力,宗教基金享受巨额的拨款,不纳税,不接受政府监管,只对最高领袖及其驻当地结构负责[13]。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教士集团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自1990年代以来便开始涉足经济领域。革命卫队通过自身的有力条件,能获得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国家外汇配给,并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他们广泛地参与到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有学者甚至认为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体量已占伊朗经济的35%,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方面,革命卫队甚至不惜与政府爆发正面冲突。2003 年,奥地利和土耳其合资公司中标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机场的运营项目,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该项目有碍伊朗国家安全,在机场开始运营时,使用武力占领机场塔楼并迫使该公司停业。最终,该机场交给了革命卫队的下属公司[14]。除了涉足经济领域之外,革命卫队也广泛参与政治。其负责人在总统选举期间会公开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或反对意见,他们甚至在选举期间利用资源,屏蔽相关地区的手机信号,使得部分选民无法投票,从而选出自身中意的总统。通过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教士集团将伊朗的经济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说教士集团把控的这些资源是伊朗神权政治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则是神权政治维系的阶级基础。以伊朗首都德黑兰为例,这座城市自北向南,从山脚向下延展开,直入沙漠。“沙漠里的人”便是城市贫民,他们从事低端的,不稳定的服务业。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在祈祷和朝圣上,生活消费则围绕着大巴扎打转。伊朗的传统社会由清真寺-巴扎-社区构成,尽管这个格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四十年里一再缩水,但大致仍延续着革命前的面貌。清真寺和巴扎一直以来都是“沙漠里的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和教育空间,这些场所无一例外由男性主导,女性则大多躲在一袭黑袍之内。周五主麻日,信徒们纷纷走入清真寺听伊玛目宣讲,这些讲话内容不仅是宗教的,更多时候是政治的,社区的清真寺扮演了传统社会民众了解国际政治最重要的场所,“Marg bar America/Marg bar Israel”(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穿插于宣讲之间的集体口号。伊玛目全部由政权委任,这些政治宣讲也服务于教士集团的利益[10]。伊朗国内的燃油和食品补贴,宗教基金会的各种救济功能,伊斯兰革命卫队优先从农村中招人,宗教作为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的唯一组织存在,这些都使得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为政权的支持者。
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总是在或快或慢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口被卷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经济力量在不断地冲击着神权体制。私人资产阶级日益发展,一批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形成。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山脚下生活着房地产商、银行家、工程师、医生、知识分子、文化名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拿着双重国籍,只是假期时回来德黑兰城北消闲。城北的周末不乏在地下空间中举行的摇滚和电子音乐演出,在家庭聚会和派对上,也总有人会带酒。这些酒或是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购得,或是自家酿造,城北包括德黑兰大学在内诸多高等学府提供着良好的现代精英教育,市中心的美术馆、图书馆、电影院、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可以满足任何西方游客的消费需求。出版界、设计界的水平都令人赞叹,艺术电影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在这里能看到的,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现代化的伊朗[10]。私人资产阶级和崛起的新中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原教士集团中的人,其生活方式,教育理念,文化环境,意识形态已经和西方世俗社会高度类似,而伊朗的神权政治,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道德警察,社会的禁酒法令,女性裹黑袍,这一系列按伊斯兰教法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对于这批“山脚下的人”显得落后和保守。他们痛恨教士集团的腐败,痛恨神权政治,他们希望变革,希望世俗化,希望与西方和解。


 一个伊朗家庭一家三代的婚礼[10]
一个伊朗家庭一家三代的婚礼[10]
教士集团的主体构成了伊朗政治中的保守派,他们着力于维护神权政治,加强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强烈地反对美国,他们维护的核心是自己这一阶层所拥有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落后的农村和城市贫民中有深厚的基础;而教士集团中的一小部分构成了伊朗政治中的改革派,他们代表着私人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宗教和政治、经济分离,进入世俗化的社会,进行私有化改革,使得他们能更加快捷地发家致富,拥抱现代文明,他们要实现的,也不过是一小撮人的利益。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还有各种中间派别,如温和保守派,温和务实派等。
两大派别在政治上的斗争从90年代就已经开始。伊朗的两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任期1989-1897)和哈塔米(1898-2005)一定程度上都是改革派的代表,他们在任期内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尤其是哈塔米,他甚至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以世俗建国,赋予公民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由改革派提出的很多议会法案,却被保守派把控的宪法监督委员会驳回,没有收到任何实效。1999年和2003年,伊朗发生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示威活动,他们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出版结社自由,均被保守派掌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镇压下去。2005-2013年,保守派的总统内贾德极力地加强宗教的统治,将很多私营化的国有部门转手交给伊斯兰革命卫队下控制的企业,因此遭到改革派的强烈反对。2009年,由于改革派认为总统选举中保守派舞弊,使得内贾德重新当选,所以改革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要求重新审查选举结果,呼吁民主政治,300万人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抗议示威,甚至有人喊出了“哈梅内伊下台”的口号,这场运动最终以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金民兵镇压结束[15]。整体而言,这一系列运动的参与者为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与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无关。而神权政治也正是依靠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把反对政权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运动一次一次打压下去。
 伊朗“绿色运动”
伊朗“绿色运动”
改革派虽然被一次一次打压,但他们的力量并不会消亡,甚至还在逐渐壮大。伊朗工业的发展,伊朗和西方社会的逐步缓和,都会壮大改革派的力量。伊朗的保守派虽然在阻挠,但他们却只能支持始于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是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共识。只不过保守派希望缓慢推进,并且尝试把将私有化的资产以另一种形式转入自己的腰包,2017年,改革派的总统鲁哈尼抱怨大多数私有化的国企落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手:“伊朗 《宪法》第 44 条政策是为了将经济交给人民和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但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将掌握在 ‘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移交给 ‘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我们甚至把经济活动交给一个拥有枪支、媒体和所有一切的政府,谁还敢跟它竞争?”[16]。
尽管有种种阻力,私有化改革还是以各种方式缓慢地进行。国企的私有化,更多地涉及到教士集团、资产阶级之间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占人口多数的大部分城市贫民和农民并未卷入其中。但是市场化改革越深入,就越会涉及到劳动人民的方方面面,伊朗政府逐步削减对劳动人民的补贴便是如此。因为伊核问题,美国对伊朗社会长期封锁,伊朗人民生活困苦。2014年,伊核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西方社会暂时解除封锁,伊朗经济有了短暂的复苏。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撕毁伊核协议,重新对伊朗进行经济,金融,军事封锁。伊朗经济结构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基础工业薄弱,美国的封锁导致石油出口大幅削减,同时国内生活必需的物资无法充分供应,这一切导致伊朗经济陷入了困境,失业居高不下,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艰难。2017年,伊朗的失业率为13%,而伊朗8000万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青人占70% ,年青人的失业率高达50%,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10%。2017年末,伊朗鲁哈尼政府公布了2018年财政预算,削减个人和企业的补贴,但是用于支持输出革命的国防开支却大幅增加,经济日益困难的时候,政府的补贴又在削减,劳动人民生活雪上加霜,不满日益加剧。2017年12月22日,伊朗鸡蛋价格上涨了1倍,引发了底层群众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走上街头,反对市场化改革。2018年,工人的罢工频发。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2017年末,伊朗民众抗议物价高涨以及高失业率
2017年末,伊朗民众抗议物价高涨以及高失业率
2020年左右的一系列事件反映的便是伊朗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场景。2019年11月,伊朗政府削减油价补贴,将燃油价格上调50%,这导致伊朗底层人的生活成本迅速上升[17],数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这是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的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斗争,他们希望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2020年1月6号,被美军刺杀的苏莱曼尼追悼会上百万人上街,展示的是伊朗神权政治和保守派的力量;1月下旬,伊朗击毁乌克兰客机而引发的上万人示威游行,则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希望哈梅内伊下台,终结腐败的神权政治,获得自由民主。
4、未来:神权政治走向何方?
从短期来看,伊朗的保守派力量仍掌握着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国家机器,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和城市边缘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军刺杀苏莱曼尼,美伊关系重新紧张,使得保守派能利用这一契机,将矛盾从国内暂时转移到国外,神权政体在短期内仍能得到维持。
从长期来看,伊朗神权政治的根基正在逐渐松动。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充分发展的地区,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才有生存的基础。而伊朗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被吸纳到市场经济的体系当中,这一切都使得神权政治的基础正在逐步缩小。教士集团曾许诺给城市贫民和农民一个伊斯兰教义中描述的公平稳定的社会,并依靠国营经济和宗教基金维持低廉的物价和微薄的福利。但是,政府已经许诺将80%的国企逐步私有化,政府已经逐步取消原有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底层人民日益陷入贫困之中。如果宗教曾经带给底层人民以物质和精神慰藉的话,那现在的神权政治带给底层人民的福利越来越少,压迫和苦痛越来越多,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日益受到市场的支配而非《古兰经》道德准则的调节,那么《古兰经》的教义也将失去曾经的神秘光环,政教合一政权的根基便会瓦解。马克思的一句话说得很精彩:“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18]神权政治根基的瓦解已经在发生。一个伊朗人2019年讲述在农村的见闻:在不久前的一次农村的主麻礼上,当伊玛目念出“我们要面朝我们的祖国,背对我们的敌人”时,现场的礼拜者纷纷扭转身体,一起把后背留给了宣讲台上的伊玛目。
教士集团在一步步的经济改革中逐步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基础,它日益成为一个和其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反对它,工人阶级反对他,一部分农民和城市贫民也开始反对他。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既然已经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农民和贫民,这些曾经维持教士统治的根基,也将加入到反对教士的队伍中去。未来的神权政治,要么被各个阶级联合推翻,要么就是教士群体保留经济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无论哪种,都意味着政权合一体制的瓦解。
只是,这种世俗化对劳动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以自由资产阶级主导下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市场化改革必然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而劳动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不会减少,阶级斗争未来也将在新的群体之间展开,伊朗劳动人民的解放之路还很漫长。
参考资料及注释:
[1] 苏莱曼尼葬礼上突发意外!至少56人死亡,革命卫队总司令誓言报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36516503310489&wfr=spider&for=pc
[2] 另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焚帝冈,面积仅0.4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1000人,国际影响力很弱。
[3] 毕健康.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J].史学集刊,2014(04):39-47.
[4] 董秀丽.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的社会原因[J].世界政治资料,1982(01):42-51.
[5] 巴扎指集市。
[6] 金彩云.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J].西亚非洲,2004(05):64-68.
[7] 董秀丽.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的社会原因[J].世界政治资料,1982(01):42-51.
[8] 海因茨·努斯鲍默 ,侯煜.霍梅尼的崛起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J].西亚非洲,1980(02):5-13.
[9] 王振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1979~2012年)[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10] 伊朗“折叠”:山脚下的人、沙漠里的人与戴面具的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66321
[11] 2017年伊朗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伊朗蓝皮书。
[12] 被利用了?掌权的教士阶层为何越来越有钱,而老百姓却越来越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820538766367863&wfr=spider&for=pc
[13] 张超. 现代伊朗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研究(1925-2009)[D].西北大学,2015.
[14]海因茨·努斯鲍默 ,侯煜.霍梅尼的崛起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J].西亚非洲,1980(02):5-13.
[15] 林友堂. 伊朗绿色运动初探[D].西北大学,2018.
[16] 王国兵,王铁铮.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J].西亚非洲,2019(06):44-68.
[17] 2018年伊朗的千人汽车保有量高达256辆,大部分人家庭都有汽车,虽然穷人家里很可能只有旧式的破车
[1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杨冰。来源:清华大学求是学会。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杨冰。来源:清华大学求是学会。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