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吕途获得了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在百无聊赖中,她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并接手负责了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她决定将目光对准打工者群体。2005年冬日的某天,吕途穿着一件蓝色羽绒服,开着手动挡的汽车,第一次来到皮村。之后她留在皮村工作,直到今天。
张慧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也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2014年,他看到皮村文学小组招辅导员的消息,自愿报名。从此之后,每周日晚的七点半到九点半间,他都会来皮村给工友们上堂文学课。通常,张慧瑜会在课堂上分享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也会和工友们一起讨论社会中的热点事件。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慧瑜老师”。
范雨素,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她住在皮村,是文学小组最早一批成员的其中之一,在课堂上发言特别积极踊跃。
皮村将吕途、张慧瑜、范雨素三个人汇集到了一起,而吕途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一书,又让他们有机会一起面对公众。在和打工群体接触时,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位置是怎样的?知识分子能否为打工者代言?打工者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吗?他们能够自我表达吗?在日前于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以《都市折叠下的新工人》为题的讨论会上,他们各自进行了阐述。
吕途:从“自带取景框”,到女工倾听者
在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附录里,吕途谈到她2005年冬天第一次来到皮村的场景。她“开着白色韩国大宇车来到皮村”,约好了一次访谈。那天,同心学校(皮村一所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全日制半寄宿学校)的暖气被冻住了,被采访对象王德志正在拿着喷火枪烤暖气片,看着这个场景,吕途非常不自在,觉得自己的访谈是在耽误王德志的时间。她由此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反思:“我不觉得我这样做出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唯一的用处是可以拿到貌似很国际化的研究舞台上去分享,但是,这样所谓国际化的东西落地到皮村又有什么用处呢?”
也有来自皮村的人曾对吕途说:“你们这些外来的研究人员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相机里面有个取景框,用固定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的认识,但是那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是被你框进去的那块世界。”
这一次短暂的皮村经历让吕途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和工友之间的距离。三年之后,吕途在工友孙恒的邀请下,致力于关注打工者的生活状况和权益问题。
2013年,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2015年又出版《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而在刚刚出版的她的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前言中,吕途写下创作该系列的原因:“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所要求的。”

创作这三本书时,吕途面对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在写《迷失与崛起》时,打工群体需要对自己的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因此《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的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到了《文化与命运》时,现实的要求是需要工人个体和整体以主人公的方式思考,建立劳动价值观,若非如此,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因此,在这本书中,吕途的预期是思考方向、出路与价值观,从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

而到了第三本《女工传记》,吕途希望记录工人群体对于生命本身的体会,希望焕发生命的力量,也要将女性个体命运和时代社会历史的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
吕途在书中说,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但她不是只写一个女工,而是多位不同年龄的女工。她的主要书写对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打工者,在最后收录书中的34个女工故事中,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曾经一度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吕途的三婶,也有1994年出生的,在高中时候被迫放弃高考,后来辍学打工的俊杰。这些女工年龄跨度达到四十多岁,她们既有迥异的人生经历,也分享作为女性的相似体验。
这34个故事延伸出两个维度的历史:时代变迁的历史和个人生命历程。吕途希望透过书中收录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有着迥异经历的女工故事,“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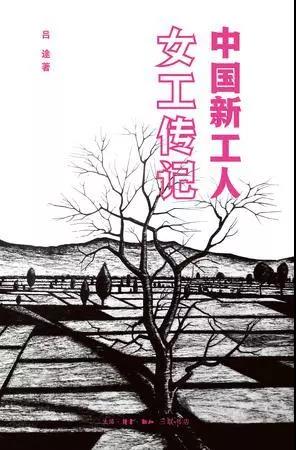
在这一本书中,吕途将目光从工人转向女工,一方面是因为她自己有直接的女性体验,二来是因为硕士期间吕途学的是“妇女与发展”专业,那时候她接触过一些理论,但都只是粗浅的理解,到后来,她自己经历了痛苦,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难的时候,才开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论。其三则是因为,在吕途看来,“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为一,不存在单一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单一的妇女解放,二者是有机的整体。正如吕途在书中所言:“我始终记得这样的论述: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是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所有压迫中最为深重的。一个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
范雨素:没有愤怒的女工,真正的女工都是穿隐身衣的
除了有吕途这种女工故事书写者,也有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中自己书写自己故事的人。在范雨素看来,吕途写的并非是女工的全景,让范雨素印象深刻的对于女工的全景式描写的作品,有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和丁燕的《工厂女孩》,“她们是用航拍的场景写的”。而吕途写的有50后、60后的国企工人,有70后的维权代表,也有90后的在公益组织工作的女性,她们都是“觉醒者”。因此范雨素说,这本书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正面力量,让打工人看到一种文化的觉醒。
接着范雨素回忆了她读到过的“女工书写”。她在8、9岁的童年里看过的一些课本,初中课本里有一篇1831年德国诗人海涅写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写的是女工。而在中国,则有解放前文学家夏衍写的《包身工》,其中的场景和现在一部分女工是一样的。此外,郑小琼也写过很多女工故事。范雨素在这些写作时间相差快百年的故事中,看到了女工们一模一样的处境。这令她感到震惊。“特别是郑小琼写的女工的眼神,都是荒凉的。”
在范雨素眼中,海涅的笔下“愤怒的女工”是想象出来的文学形象,那样的女工并非文学的镜子,真正用文学清晰反映的,是郑小琼和夏衍笔下的女工,她们是无力的,穿着隐身衣的。
由此范雨素也想到主流媒体话语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两个女工的故事。一个是在1996年被广泛报道的一位公交售票员,还有一个是2013年引起广大关注的人大代表刘丽。她们一个是国企工人,另一个是农民工。前者是一个国家主人公形象,很正面也很正能量,而后者则是一个悲凉的故事:刘丽本是一位洗脚女工,拿工作中赚的钱帮助留守儿童上学,后来因为她的这份爱心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范雨素认为,这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听起来像听国歌似的,而另一个听着像一些民谣歌手唱的悲情民谣。”她还听到了很多家政工的故事,其中一位和范雨素年纪差不多大,有三个孩子,长期在一个家庭干,不敢辞职,因为一旦辞职,找工作的间隙就没有收入。她跟孩子有7、8年没有见过面,挣的钱都寄回去给孩子上学,她老公打零工用她挣的钱支撑家庭。每次一想到她的故事,范雨素心里就很难受,“她是一个母亲,长期和孩子不见面,她天天是用什么心情在劳动呢?所有做母亲的人都能想到这个故事的悲凉。”
更进一步,范雨素认为这个家政工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社会样本,因为很多的农民工都和她一样,长期劳作,把工资寄给家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供孩子上大学,从此改变命运。但范雨素提出一个疑问:我们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能改变命运吗?她现在经常看到报纸上和杂志上有一句话,大学毕业等于0。母亲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亲情,每天在撕心裂肺地想孩子,用亲情换来的钱让孩子上学。可是孩子的父辈们,孩子的母亲却失去了亲情,失去了母子的爱。一方面他们想见到孩子,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出去接受教育,改变命运,将来能赚钱。“可惜,现在大家又在说大学毕业等于0,就有了很多伤心哭泣的母亲。”
看到这样的事例,范雨素觉得迷茫无力,“我看到和我一样的农民工、家政女工,都是和我一样是迷茫的、无力的,我们这些人民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
谁在言说?为谁代言?出路何方?
从吕途为女工立传的努力到范雨素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的自我书写,这其中涉及谁在言说,谁为谁代言的问题。
在张慧瑜看来,这个问题与20世纪的历史非常相关,即怎样从自我走向更广大的群体,走向他人,走向其他的社会阶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一直在讨论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左翼实践中的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自80年代以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代言问题:我们只能写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多作家只能看到“我”所看到的真实,而不能替其他人说话,这种代言的困境的背后,是整个左翼的革命实践的失败。而吕途恰恰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最朴素的可能,就是要试图走出自己,去倾听、去了解,去对话、并在对话中得到相互理解。
“这种倾听和对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她给我们展示的不再是一些伟人的故事,不是英雄的故事,不是丰功伟绩的故事,而是身边的普普通通的最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倾听的视角,是普通人的角度。这本身我觉得就是很有历史和文化意义,因为我们可能会知道,历史是有权力的人来书写的,是胜利者的清单。从古至今无辜的平民大多数都不在历史中,我们图书馆中找到的典籍都是那些曾经的伟人,曾经掌握权力的人给留下的。所以这个意义上,吕途老师试图用她的工作,让更多的人、更多无法发出声音的人,把他们的故事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工作者的任务。” 张慧瑜说。
除了知识分子的倾听和理解,打工者能够自己为自己代言吗?他们能够自我表达吗?
张慧瑜由此联系到范雨素说的隐身衣问题。在张慧瑜看来,这件“用廉价料子制成的隐身衣”,是社会的隐身衣,社会让新工人这个群体隐身起来,就像建筑工地上覆盖的那些绿色帷幔一样。同样隐身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厂和车间。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意思,如果再引申一下,隐身衣的隐喻是工人无法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只能被别人代表。美国文学理论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曾经讨论过“底层能言说吗?”在她看来,底层不能说话,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话语,并不是说他们不说话,而是他们说了主流社会也听不见。主流社会编织了一个隐身衣的屏障,将他们压缩在第三空间中。我们无法看见他们,或者说我们即便看见了,也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面对这种情况,范雨素认为可行的方法是自己为自己代言,“每天为自己写文章,每天发在公众号上,我们会被别人看见的话就不是穿着隐身衣的人了。”
而作为一位既在高校任教,同时又在皮村指导工友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型知识分子,张慧瑜表示,对文化劳动者来说,这十年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就是知识劳动和文化劳动在急速地贬值。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都是工薪阶层,挣的工资很难在支撑他们在城市过上好的生活,因此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同病相怜的,他们构成命运的共同体。因此改变工人的命运也是改变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只有所有劳动者的命运都改变,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出路何在呢?在吕途看来,她接触的很多工友都是迫不得已在漂泊,都被动认同了一种过客心态。这种心态最适应的是资本的逻辑,因为资本希望每个人此时此刻都是过客,以便资本对人进行更好的剥夺。“资本一路走过来,它拿走了它想要的东西之后,留下的就是一片废墟。”吕途认为,一直按照资本的逻辑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们不能认同那样的一套逻辑,我们一定要创造我们一套不同的逻辑。
反资本文化的出路有哪些呢?吕途认为要有团结经济,可能是在城市的社会企业,可能是在农村的合作社。这是吕途在工人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我们觉得,既然都特别迷茫,何不去尝试一下呢?”吕途说。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傅适野。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
(作者:傅适野。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