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们对他们本国发生的革命事变所持的观点。回望恩格斯笔下这些无比激进、动不动以唯我独革自居、满嘴“消灭剥削”豪言壮语的左翼小宗派及其表演,正好与20世纪孕育出的极左翼托派分子相映成趣。
 图片来源:网路
图片来源:网路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使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图片来源:网路
图片来源:网路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 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作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 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高见。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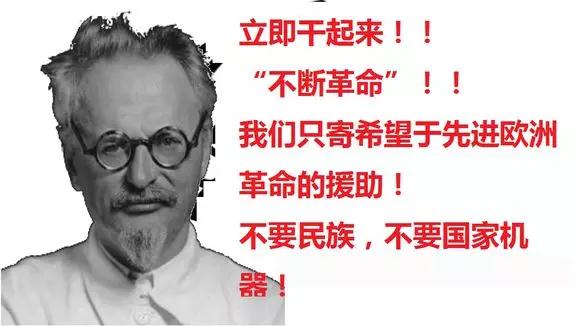 图片来源:网路
图片来源:网路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陷入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认为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说恰好无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这是必不可少的信仰象征。
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
于是,这三十三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 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么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图片来源:网路
图片来源:网路
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作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作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恩格斯。来源:摘自《流亡者文献》)
(作者:恩格斯。来源:摘自《流亡者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