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种长期不关注综艺至今分不清迪玛希和迪丽热巴的区别的人来说,要不是好几个朋友盛情推荐,我压根不知道最近有个叫赵雷的民谣歌手火了。听说是唱一首叫《成都》的歌唱火的,而且火得那叫一个一塌糊涂。我赶紧回家诚惶诚恐地搜了搜(其实并没有搜,因为网易云音乐一打开,最先跳出来瞪着我的就是赵雷),听了,是不错。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我与另一个喜欢民谣的朋友谈论起《成都》这首歌时,他立刻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跺足道:“唉,你别提了!我刚从成都回来,那里满大街都在放这首歌,我真的不想再听了。”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还记得几年以前,我们还在县城读高中,那正是《小苹果》横空出世一夜之间占领全城大大小小所有有音响的门店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正在一整条循环播放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的步行街中穿梭时,正是这位朋友郑重其事地问我:“你听过《南山南》这首歌吗?”见我摇头,他说:“推荐你听一听。挺好听的。歌词也很好。”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还记得几年以前,我们还在县城读高中,那正是《小苹果》横空出世一夜之间占领全城大大小小所有有音响的门店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正在一整条循环播放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的步行街中穿梭时,正是这位朋友郑重其事地问我:“你听过《南山南》这首歌吗?”见我摇头,他说:“推荐你听一听。挺好听的。歌词也很好。”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打开了《南山南》。浓重的北方口音,饱含沧桑的老烟嗓,安静而忧郁的旋律,以及语焉不详的歌词,瞬间就俘虏了我那听惯了“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的双耳。我立刻在南方看不见月亮的深夜里感受到了一种在“艳阳里大雪纷飞”的凄美感,并产生了“他戳中了我的心事”的错觉(虽然我并没有听懂歌词)。我又反反复复地听了好几遍,然后认真地品读了一下歌词,最终在“有人和我有一样的忧郁”的欣慰和“我看不懂歌词说明我还不够忧郁”的羞愧中纠结地睡去。
 在那以后我听了很多民谣,从“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到“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从“我来过你的孤独与倾听,你一微笑我就失言成一叠长信”,到“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那时的我觉得,民谣是一座孤岛,岛上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凡夫俗子勿入”.所以当毕业后和一大群同学去KTV,发现几乎全班都会唱《南山南》并表示都很喜欢这首歌时,我顿时感到十分挫败,放佛亲眼目睹“情怀”这个圣洁的词汇遭到了一群老粗的强奸,再也无法用来证明自己了。
在那以后我听了很多民谣,从“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到“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从“我来过你的孤独与倾听,你一微笑我就失言成一叠长信”,到“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那时的我觉得,民谣是一座孤岛,岛上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凡夫俗子勿入”.所以当毕业后和一大群同学去KTV,发现几乎全班都会唱《南山南》并表示都很喜欢这首歌时,我顿时感到十分挫败,放佛亲眼目睹“情怀”这个圣洁的词汇遭到了一群老粗的强奸,再也无法用来证明自己了。
赵雷火了以后,有人总结了民谣的套路,说民谣的歌词里高频出现的总是理想、流浪、姑娘、青春、南方这些词儿,时不时还混杂着性暗示和脏话;而民谣歌手往往有着混乱的生活作息、要么得不到要么得到了也不知为何必然会分离的爱情、窘迫的生活状态和与此相对应的永不磨灭的希望,他们的情绪宛如季节变迁,在春天感到快乐,在冬天感到孤独。
其实现在我仔细一琢磨,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当我唱着“流浪”、“远方”,口齿不清地骂着脏字儿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恶和鄙视。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益,为谋一份好职业竭尽钻营算计之能的人不同,我还有“理想”,虽然我并不能确切知道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大概就是一辈子唱着“流浪”和“远方”?),但我确切知道它面临着很多阻碍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反正坚定的方式也无非是时不时地唱一唱理想,在失眠的凌晨为之象征性地掉几颗泪。中学阶段泯然于众人之中的我,身体里那青春的全部力量、幻想、不羁和激情……在学习和考试面前卑躬屈膝,却在民谣里获得了理解和呼应,是民谣让我相信自己是“独特”的、不甘被驯服的,这成了我必须牢牢握住的尊严。哦对,歌里还有“姑娘”,我的温柔乡,我不知道她是谁,长什么样;班里的姑娘总是穿着校服放学一起卖辣条吃,只有歌里这个神秘的她令我魂牵梦绕心绪不宁。不过正如我生命中想要的任何东西一样,她总是不属于我,我总是得不到她。这种得不到竟构成了她的美……她和那个抽象的“理想”一样(甚至有时他俩就是一体的),浮在 “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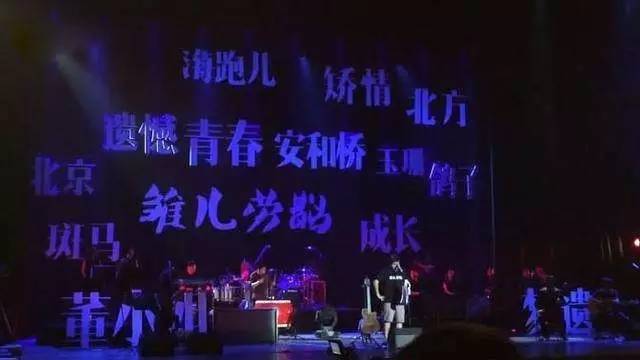 然而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走向他们呢?民谣从来没告诉过我答案。当然高中时的我也从没细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习惯一边戴着耳机哼着歌,一边写着我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然而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走向他们呢?民谣从来没告诉过我答案。当然高中时的我也从没细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习惯一边戴着耳机哼着歌,一边写着我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逃离现实的冲动,在民谣里仿佛都获得了合理性。民谣告诉我,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小日子,众生之苦无非是各自生命的劫难,日后会酿成酒和蜜。人生在世上难免诸多不自由,内心却尽可以一马平川恣意流浪。我用耳机把自己和亲戚朋友钻营世故的生活隔开,和电视里关于房价、码农的新闻隔开。高中的苦日子就这样挨过去了。虽然梦想弹着木吉他流浪天涯,但我却总是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刷《五·三》,我把这当做歌里唱的年轻时候必经的忧伤,过了这个坎儿,我就可以去找我的姑娘。
然而痛苦的是,无论何时,现实又总是大过情怀。进入大学,坐在梦想的教室里,我依然忍不住听着民谣,在孤单的时候落泪,并且发现身边有一众好妹妹和宋冬野的拥趸者。
我开始纳闷,在学校里蹲了十几年连女孩儿的手都没牵过更不曾走上一生去拥抱谁的我,到底在忧郁些什么?为什么四肢健全年轻气盛成绩优异轻松拿下985的我听几首民谣就忍不住想流泪,长期沉浸在“没有人懂我的忧郁”的痛苦和怕这种忧郁真的被人懂了就变得庸俗的矛盾中?
回顾我的大学生活,它其实和高中时预想的自由其实截然相反。虽然我梦想周游世界,在某个落日的村庄邂逅我那位心爱的姑娘,但我还是选择了每天早起刷托福,大二的假期就忙着实习身着西装标准笑容回答面试官的问题。在可以预期的毕业后的生活里,找工作、车、房、结婚、生子、养老、看病……随便一座大山就足够轧断我的脊背。我像只蚂蚁一样终日不停,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一首民谣当做自我安慰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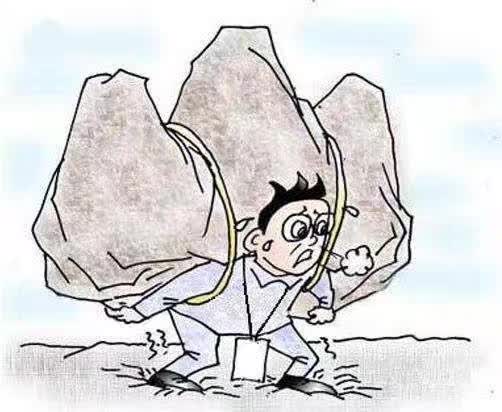 更刺激我的是,班上开奔驰来上课的北京同学,挂了四科也一样云淡风轻,而我考试前夜的凌晨三点还在通宵教室自习。真正“成功”的人是不听民谣的,他们才是假期去周游世界恣意把妹的人。某天亲耳听见我爱慕的女生说“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嫁到北京二环的四合院里头去”。
更刺激我的是,班上开奔驰来上课的北京同学,挂了四科也一样云淡风轻,而我考试前夜的凌晨三点还在通宵教室自习。真正“成功”的人是不听民谣的,他们才是假期去周游世界恣意把妹的人。某天亲耳听见我爱慕的女生说“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嫁到北京二环的四合院里头去”。
所谓“理想”,就TM这样一文不值,碎了。
也许赵雷的成功就在于他虽然姓赵却唱着不配姓“赵”的人们的故事:“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这样的歌要是让王思聪来唱就很没意思了。当然,如果让一个农民工来唱,也很没意思。农民工照例是被认为不配有“理想”或者“情怀”的。只有我们这群小资,这群自认为应该是winners的losers,不甘心生活的沦落、眼前的苟且,却又在1%和99%不断拉大的现实中不可逆转地沦落着、苟且着,才会唱起这首歌,泪流满面。
原本以为自己在橄榄核的中央,在实习单位加班,每天挤两次十号线的现实却让我意识到自己正从上而下一点一点地坠落。企图像一个天之骄子一样去谈论梦想,仗着饱暖思文艺,却发现双手已牢牢地被生活绑架,和以往不屑的碌碌众生无异。会吟诗,想去远方,却不知哪一天出门嫖娼会死于非命。唱一唱民谣就权当反抗,一边感伤,一边妥协,直到被嵌入麻木的体制内,还要自以为是的悲壮。
我开始明白,在这个意义上,民谣也是鸡汤。有人说赵雷火是因为他的歌打开了人们情绪的闸门。但是,小情小爱小迷茫小感动,这并不是我情绪的全部。当我逐渐成长,逐渐单枪匹马地面对如怪物一般庞大的社会,逐渐透过它黑暗的外表洞察它更加黑暗的内在时,我突然明白,比起那种淡淡的忧郁,我对这个世界更多感到的是愤怒。我愤怒我们穷尽一生都走不到另一些人的起点,我愤怒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愤怒现实残酷社会黑暗阶级固化官僚弄权才把我们都变成了我们讨厌的样子。但民谣从不表达愤怒,它以无谓的心灵寄托把我们从刨根究底的道路上劫持了下来,索要了寄托费之后便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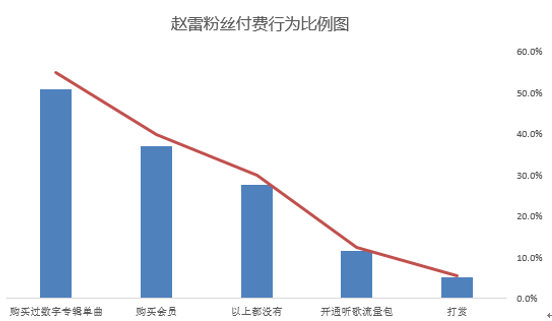 于是我感到更加愤怒。我的生活像一团肮脏的纸被人肆意揉皱,我在这城市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但我不想再就着几口兰州一把破琴便把耻辱编成意淫的诗。我想,当有一天我们不再美化穷,而是正面“我们为什么穷”这个问题时,愤怒而团结的歌声将会比民谣更加动听。
于是我感到更加愤怒。我的生活像一团肮脏的纸被人肆意揉皱,我在这城市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但我不想再就着几口兰州一把破琴便把耻辱编成意淫的诗。我想,当有一天我们不再美化穷,而是正面“我们为什么穷”这个问题时,愤怒而团结的歌声将会比民谣更加动听。
(作者:老四。来源:公众号“思行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