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人似乎偏爱这个词,悲惨—misere,从雨果到今天谈论大选的知识分子,它始终是个高频词。
法国人似乎偏爱这个词,悲惨—misere,从雨果到今天谈论大选的知识分子,它始终是个高频词。
背后的原因,当然并非对这个词本身的“偏爱”这么简单。
“被遗忘的工薪阶层”的声音在英美,这两大传统资本主义桥头堡,以巨大的动静重新被世界听见后,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政客们便纷纷寄望借势在今年的德国、法国、荷兰复制这一胜利。
去年年中,美国一本回忆录《山里人的挽歌》登上纽时畅销榜,而作者名不见经传,是一位从锈带走出来,名叫旺斯的年轻人。这本书被诸多媒体誉为“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川普的胜利”(参见大家往期文章《美国底层白人的日子有多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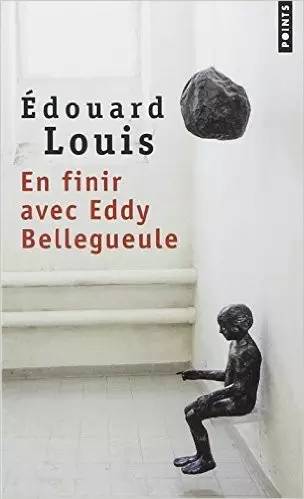 ▲ 《埃迪的结局》封面
▲ 《埃迪的结局》封面
其实在《山里人的挽歌》之前,2014年法国出现过一本自传小说《埃迪的结局》(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类似的,作者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也名不见经传,也出自衰败的偏远工厂小镇,而那本书,也轰动地进入公众视野。
相比《山里人的挽歌》质朴的悲情审判,《埃迪的结束》更展现出作者路易非凡的文学天赋,以及具有十足法国味儿的知识分子激进思考。出版时路易仅21岁,当年就卖了30万册,并进入文学大奖龚古尔的最终候选名单,同时在法国引发了围绕阶层、贫穷、性别不平等以及种族歧视的激烈讨论。
他说,写这本书,是为了替工薪阶层发出声音,“为他们而战,因为,他们似乎已经在公众视线里彻底消失”。作为处女作,《埃迪的结局》所触碰的是绝对的硬货,它毫无保留地在涉及到的每一个话题里重拳频出。书中描述的童年生活,处于被文化政治精英所主宰和藐视的阶层,在路易看来,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忽视甚至无视,直接导致了极右势力的崛起。
我的阅读过程,始终笼罩在不安和恐惧当中,随时担心,这恐怕才只是冰山的一角吧。然而当我合上书那一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真实的生活只会比这更凄惶。
 ▲ 爱德华·路易
▲ 爱德华·路易
故事发生在索姆省阿朗库尔(Hallencourt, Somme),一个与世隔绝的工厂小镇,1300人口,路易就在那里出生、长大。贫困线以下的人生,像传说一般荒凉,还有他父亲酒醉后的暴力为之添加注脚——那是被生活羞辱的工薪阶层男性无处发泄的愤怒。
故事从一个特写镜头开始,十岁的埃迪在一所小学校的走廊里遭遇袭击,接着是一串令人喘不过气的快照场景,呈现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由愤怒、暴力、酒精组成的日常生活。这对于埃迪这样气质柔弱,像女孩儿一样的男孩,世界就是一场暴风雨,让人根本不相信他会活得下去。
在这样一个粗砺的后工业地区长大,他很小就明白了一件事,政治,并不是在一个盒子上放上十字架那么简单。当他母亲一面挣扎着面对失业加酗酒的父亲,一面用微薄的救济金养活全家时,她会念叨从前的日子,“左派当权的时候,我们的盘子里有牛排。”
如今,距离法国大选还有三个星期,像法国绝大部份的社会底层人士一样,他的父母,正小心翼翼地在倾听着这位新的穷人捍卫者——玛琳·勒庞以及她的所有承诺。她保证要还一个富裕的法国,给法国人。与那句让美国白人工薪族热泪盈眶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如出一辙。
 ▲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东方IC供图
▲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东方IC供图
如今的路易,已逃离那个阶层,拥有傲人的巴黎高师文凭,踏入了漂亮时髦的巴黎知识圈,可这个经历反而更加令他坚信,政治对于他母亲常说的“贫穷小人物”,依然是一个诅咒。
政治这个词,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含义。
“在社会底层,政治一直都是事关生死的问题。最让我父母担惊受怕的就是失去那一点救命稻草私的社会福利。贯穿我整个的童年记忆,政治可以改变一切。我们的生活一直紧随政治的节拍,它就像悬挂在那些卑微生命上空的风暴。现在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样的风暴在富裕阶层的头顶上空并不存在。”
这是他来到巴黎后,最令他震撼的一个发现,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们,没有蒙受政治的诅咒。在巴黎的布尔乔亚人群中,政治绝对无关生死,无关是否有饭吃,病人是否能就诊。政府无论左右,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吃饭。在这个世界里,政治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被谈论,不被记起的,不存在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像发生在穷人身上一样的变化。
路易在一次采访中,坐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记者注意到他说话时强忍着随时可能爆发的狂怒,桌下的双腿一直在颤动。
既然政治的结果,对于那些掌控和玩弄政治的人不会产生丝毫影响,而只会对路易童年生活中的那一群人产生事关生死的冲击,它怎么可能创造出更好的生活?
他告诉记者,在家乡那个村子里,50%—55%的人会投票给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谢天谢地还有弃权的,否则这个数字会在70%—75%。这些人支持FN,因为他们这些年被排除在世界的繁荣之外,忍受贫穷,被遗弃。她母亲投票给FN,给玛琳·勒庞,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肯和我们说话的人”。他们感到自己被忘记了,所以他们要找人去投奔,那个人就是玛琳·勒庞,那个他们认为愿意倾听他们疾苦的人,那个他们相信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好的人。
人们都在说她会赢,可那根本是因为,原本代表像路易母亲那样的人的左派,已经将他们抛弃了。曼努埃尔·瓦尔斯、弗朗索瓦·奥朗德,正是他们,把那一群人置入今天的境地。人们其实从不指望右派能为底层谋利,可是左派……左派已经不再谈论贫穷和困苦。
说到暴力,路易有另一层解读。
直到1980年代初期,他的故乡一直有一个本地工厂几乎雇佣了当地所有的居民。到他出生时,也就是1990年代,开始了裁员风波。许多居民因此没有了工作,依靠福利勉强维生。他的父母都是十五六岁就离开了学校,他的祖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也大抵如此。父亲在厂里工作了十年,母亲一直没有工作,因为父亲坚持,女人的职责是在家里照看孩子。
文学是人们绝不关心的事。他们会在电视里看见文学奖,但那些书里说的事大多与他们无关,出版物从总体上来说,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他的母亲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小人物,没人对我们感兴趣。
那是一种在他人眼里压根不存在的感觉,国民阵线在那里获得超过50%的投票,这些选票超越了种族和任何其它原因,只是绝望后的挣扎,想要让自己存在,被其他人注意到的无妄挣扎。
文化,教育,书籍,所有这一切,通通给予他们被拒的感觉,作为回报,他们也拒绝这一切。所以你永远不能说,底层拒绝文化,因为那恰恰是文化拒绝了底层之后得到的回报。同理,你也永远不能说底层喜欢暴力,正是因为底层遭受了日常生活施加给他们的暴力,
所以他们复制暴力,投票给国民阵线便是一例。应该对此负责的并不是他们,而是社会的治理阶层。
路易用他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文化可以怎样转化为暴力,他自己怎样利用文化,去伤害身边的人。他是全家第一个进了高中、大学的人。高中时要么住校,要么去朋友家借宿,到周末才回父母家。每次一走进家门,就拿本书坐在沙发上,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假装在读。仅仅是希望让家人知道,他跟他们不一样,再也不属于他们那个世界。那时的他,知道一本书是他可以用来达到那个目的的最凶狠最暴力的武器。
如今他为自己的残忍和傲慢而羞愧。可那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离开。母亲与他的争执中,语气里混杂着愤怒、哀伤和恶心,他却把这些通通视为褒奖:终于,我属于那个人们会读书的世界了。
路易的写作正是源于这些空白和缺位,因为他不能在任何一本书里找到自己童年生活的世界。黑人女性有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他的世界没有那么好运,没有找到自己的莫里森。只要大比例的书籍仍然是写给特权精英的,只要文学还在继续形成对他母亲那一群人的羞辱,这个文学小天才居然说,“文学可以去死了,我会一脸漠然地看着它死去”。
是的,包括小埃迪在内,路易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经意的种族主义者。他自己更是性别歧视,性倾向歧视的受害者,作为人们眼里的“废柴”,“同志”,“娘炮” ,他一再被事实提醒,他是底层里的底层,连“阿拉伯人”,“犹太人”,“阿尔及利亚人”或者“黑人”都不如。
路易没有因为父母、老师和邻居的冷漠或残忍而指责他们,他们是作恶者的同时,也是同样程度的受害者。他们的恐同、性别歧视、酒瘾毒瘾、残忍、种族歧视以及暴力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为被掠夺和被忽视的联合作用结果。
全书的口气让人吃惊地冷静,往往在感情激烈或者叙述最流利时,忽然语结。有时会有突如其来的一道柔软闪电将你击中——而且经常指向埃迪那位伤人也自伤的父亲——所以当他告诉你,有些段落是用眼泪写就时,你相信他。在事实面前,没法退缩,但伤感也没有用。
路易成名后与家人关系紧张。其理由非常耐人寻味,那就是寻求共同语言的挑战。而面临这一挑战的,并非显而易见的作家群体,而是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包括自媒体。
用路易的例子来说,他是应该利用明显具有优势的主流语言来描述被主宰的人群?还是使用他童年所熟悉的,那个将他称作可悲可耻的“废柴、娘炮”,充满暴力的语言?怎样找到一个新的声音,一种全新的讲述方式?使得每一句话都是对主流社会的提醒,不要忘记像路易的父母,像难民一样的个体。对他们来说,政治依然事关生死。
(作者:黑爪。来源:公众号“大家”,本文原标题为《法国的新“悲惨”故事》)





